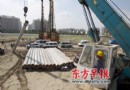英國園林 為自然而革命
日期:2016/12/14 11:33:06 編輯:古代建築 這是一場徹徹底底的革命。在世界園林史上,恐怕再沒有比18世紀的英國更為堅定的革命者了。

風景畫與中國風
上圖不是一張風景畫,而是英國切茲渥斯莊園花園的一角,鮮花、樹叢、溪流、山石,都富有野趣。在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主義思想影響英國,追求自由的英國人完全摒棄了此前規整的幾何式園林,重新發現自然,追求自然之風。這與中國士大夫在園林中的追求相近,於是中國風也始終影響著英國園林。
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君主專制時期,英國園林脫不開意大利和法國的影子。可到了18世紀,一切都被顛覆了。綠色雕刻、圖案式的植壇、幾何式的規則格局被干淨利落地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派自然風貌。美國散文家歐文在《英國鄉村》中有一段優美的文字,將這種自然風致的英國園林描寫得十分真切:
景物的妍麗確實天下無雙。那真的是處處芳草連天,翠綠匝地,其間巨樹蓊郁,濃蔭翳日;在那悄靜的林薮與空曠處,不時可以看見結隊的鹿群、四處竄逸的野兔與突然撲簌而起的山雞;一灣清溪,蜿蜒迂徐,極具天然曲折之美,時而又匯潴為一帶晶瑩的湖面;遠處幽潭一泓,林木倒映其中,隨風搖漾,把水面的落葉輕輕送入夢鄉;而水下的鳟魚,往來疾迅,正騰躍戲舞於澄澈的素波之間;周圍的一些破敗的廟宇雕像,雖然粗鄙簡陋,霉苔累累,卻也給這個幽僻之境添了某種古拙之美。
“雖然沒有斷頭台和內戰,沒有清教徒的狂熱和克倫威爾的鐵腕,但是它同樣需要有反傳統的斗爭,有這斗爭所需要的自覺性和勇氣”,清華大學建築學家陳志華如此評價這場造園藝術史上空前的大革命。那麼,這革命的自覺性和勇氣,又來自何方呢?
重要的思想基礎是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主義,其時,哲學、宗教、政治、文化一切領域都醞釀著革新。在造園藝術方面,文明與自然的利弊得失,幾乎成為思想家們熱切關注的問題。

此圖是維爾頓府裡的中國橋。
生活在16、17世紀的思想家培根,早就思索過這個問題。在《訓示》一書中,他批評了古典花園裡“對稱、修建樹木和死水池子”。他在《論花園》中設想了一個30英畝的花園,其中有6英畝是“自然荒野”,“處處有花兒開放,並不規則”。培根是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否認先天理性的至高無上,相信感性經驗是一切知識的來源。這種與古典主義背道而馳、強調想象與情感、追求放縱自由的潮流,為英國造園革命准備了哲學和美學的基礎。
有了這個基礎,資產階級革命對於舊制度的抨擊,立刻也在造園藝術上找到對象,即古典主義。此時,作為宮廷文化的古典主義失去了其政治基礎,規則的幾何式園林被視為專制、壓迫和強權的象征,是必然要被革命的。
而自然神論者的身份,又讓18世紀思想家們對文明與自然孰優孰劣的探討毫無懸念。他們反對一切不自然的東西:幾何布局專橫地硬加給不同地形,規則修剪是限制樹木的自由生長,用壓力逼迫水柱噴向天空則違反了自然物性。對自然的奴役,也和專制制度對人的奴役一樣,無法被當時的英國人容忍。
另一方面,經過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天主教會和舊貴族的大批土地轉到了新貴族和農業資產者手中。而18世紀英國的自然風致園,就是從這些新貴族的牧場和農莊裡生長出來的。在陳志華所著《外國造園藝術》中對此闡述得很精辟:
他們大多是輝格黨人,溫和的啟蒙思想家,鼓吹民主自由和憲章運動。他們的造園藝術理論是他們哲學和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他們反對圖解專制政體的幾何園林,提倡象征自由的不規則園林;他們認為修剪樹木成綠色雕刻是對天性的戕害,而讓樹木順乎自然的生長,則是“推人及物”的博愛之道。這些新貴族的文化教養很高,都是文人、學者、政治家、思想家等一時俊彥。他們不但躬自造園,而且著書立說,建設造園理論,所以使這場造園藝術的革命聲勢浩大,半個世紀裡,就波及整個歐洲,打敗了足足有兩千年歷史的傳統。

自然的魂靈
古老的建築,鑲嵌在郁郁蔥蔥的樹林中,藍綢緞一般的河流蜿蜒其前,一團團的白色羊群點綴著黃綠色的草地,與天空中的白雲遙相呼應,這樣的場景大概很難讓人與園林聯系起來,但它確實是英國切茲渥斯莊園花園,屬於自然風致式園林。這類園林注重自然的魂靈,將田野風光和遼闊樹林等都收為園景,對近代城市公共園林有很大影響。供圖/TPG
這或多或少會令人想起中國士大夫以及他們的園林。確實,反對封建專制、憎惡君權和禮教束縛,向往自然狀態,是中國士大夫和18世紀英國新貴族共同的追求。也正是因為如此,18世紀的英國造園藝術對中國園林倍加推崇,毫不誇張地說,其形成和發展始終是在中國造園藝術的強烈影響之下。
1685年,英國的政治家、作家坦伯爾爵士曾寫了一篇《論伊璧鸠魯的花園,或論造園藝術》,盛贊中國園林之美:“運用極其豐富的想象力來營造十分美麗奪目的形象,但不用那種一眼就看得出來的規則和配置各部分的方法。”坦伯爾還為中國園林杜撰了一個形容詞“Sharawaggi”,它意味著千變萬化?抑或是詩情畫意?18世紀初,為自然風致園林奠定理論基礎的造園家艾迪生,也看到了這個詞,他的闡釋可能更為貼切:“乍一看便使人浮想聯翩,只覺得美不勝收而又不知其所以然。”這,恰是艾迪生和18世紀英國人的審美追求。
可惜的是,當年的英國園林保留至今且未經大規模改造的幾乎沒有,在某一些園林裡或許還殘存有一些局部。比如,豪厄德莊園和勃侖南莊園還能看出些許當年的痕跡。這兩座園林是18世紀初造園家凡布婁的代表作。
在建造勃侖南莊園時,曾有人問凡布婁該如何設計?他答道:“去請一位風景畫家來商量”。風景畫是自然風致園林追求的境界,而詩歌也同樣被請進了園林。詩人沈斯東曾說:“自然風致園可以搞得像一首史詩或一出詩劇”,他在自己的李騷斯花園裡,設計了一個環形的游覽路線,說是“引導人們從詩中穿行”。
還有一處造園細節值得一提,那就是“哈哈牆”。說是牆,其實只是一道壕溝,也稱干溝。游人隨著興致四處游覽,能賞到近景,更能極目遠眺,待走到干溝前才發現不能前行,於是哈哈一笑,哈哈牆由是得名。作為園林的邊界,由圍牆到壕溝之變,正說明了英國園林對自然的追求。18世紀後期,被稱為“自然風致式造園藝術之王”的造園家勃朗,干脆連干溝也不要了,花園和自然之間再無界限,融為一體。至此,自然風致園林完全替代了規則的幾何式園林,甚至沒有留下一丁點的舊痕跡,並一直影響著近代的城市公共園林。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勃朗設計的斯道維花園,園中一個哥特式教堂門上的銘文如此寫道:“感謝上蒼沒有生我為羅馬人”。不妨套用這句話,“感謝英國曾為自然而進行的園林革命”。
(來源:中華遺產)
- 上一頁:日本園林 永恆與枯寂
- 下一頁:法國博物館為了游客一直在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