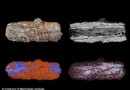遺址公園:保護不好不如不建
日期:2016/12/14 10:54:07 編輯:古代建築


杜金鵬

魯國故城遺址公園的拆遷問題並不明顯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考古是件很神秘的事情。如果不是有新聞報道或者網絡小說,幾乎沒有人能一窺考古的面目,能看到的,只有作為考古成果的博物館文物展示。從2010年開始,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以下簡稱遺址公園)的推出與開放,讓普通大眾有機會直接接觸到考古與文物本身。2014年,對於遺址公園的運行,國家文物局組織專業機構及人員進行了評估。作為評估人員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鵬教授在欣喜的同時,也發現了不少問題。他擔心,如果過於急功近利,遺址公園還不如不建。文/圖記者窦昊“考古人沒朋友”
考古文物界歷來思想保守封閉,遺址公園的建設打破了這一規律
作為一名從事考古工作多年的專業人員,杜金鵬表示,文物考古界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封閉的群體,不希望外人參與考古工作,甚至連圍觀都不被接受。具體表現就是,但凡文物考古現場,都會用施工擋板或者鐵絲網圍起來。這樣一來,雖然能夠防止外人來破壞,但卻阻隔了大眾了解考古工作的機會。同時,對於新聞媒體的采訪考古人也有著互相矛盾著的心情:一方面,對於宣傳個人成績及團隊工作,希望媒體報道;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讓大眾過於了解。因此,考古界與新聞媒體的互動常常是被動的、生澀的,有時候因為信息的不全面,還造成了不必要的誤會。作為一名畢業於山東大學的山東人,杜金鵬認為,山東考古界這一方面尤其需要改進。
不僅如此,考古人的封閉還表現在對同行的隔離。“我們的考古材料,就算行業內的人互相看看都困難。”杜金鵬說,“比如我們社科院的考古人員去地方上考古,挖了一堆東西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留下一堆擦屁股的事給地方上,人家肯定會有意見。”有鑒於此,文物考古界在各個層面上都鮮有朋友。杜金鵬說:“我們對文物的保護往往就是各級文物局一家在叫喊,其它部門跟你配合的很少,跟我們對著干的卻比較多,比如規劃、建設、財政等。”
越是封閉,越是加重了考古人的“自娛自樂”。“很多時候,我們把考古遺址當作了本部門、本行業的內部財產。”杜金鵬表示,遺址公園的推出,對於文物考古界改變保守的思想有很大好處。“遺址公園讓文物考古打開了大門,吸納更多的部門進來,把大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充分調動起了積極性,這對我們的工作是有很大幫助的。”
另一方面,在遺址公園的推動過程中,考古人也更多地與整個社會接觸,不僅從認識上更加全面地了解文保工作的現實,更從學科上開始重新審視考古專業本身。
投資的與業余的
地產開發商投資遺址公園建設、違背考古文保規律的建設帶來很多問題
以西安大明宮與隋唐洛陽城的遺址公園為例,他們之所以能夠進行巨量的拆遷工作,是與其吸納的資金的方式密切相關。“這兩個遺址公園基本上就是用房地產開發商的錢進行拆遷,用國家文物局給的錢進行建設。”杜金鵬說,“既然人家拿了拆遷費,那很多事情就不能按照考古人的想法去推動了,商人畢竟是逐利的。”
相關數據顯示,大明宮遺址公園的投資達到120億元。而十一五期間,國家文物局給100處大遺址總共投了100億資金,像大明宮這樣的項目平均一個才1億元。因此,對於像大明宮遺址公園這樣的項目,是商業資金在主導,“遺址公園是公益的,但商人投資不是做公益,他們是要講回報的,因此這裡面就產生了悖論。”
以隋唐洛陽城為例,當初開發商花了10億元拆遷的用來建設遺址公園的地塊,如今規劃裡顯示,只有20%是用來遺址保護的,剩余80%用於地產建設。“專家們肯定不同意——這不是讓遺址公園成為點綴,實際上你們是要蓋商品房了嘛。所以規劃至今擱置無法動工。”杜金鵬說。
不僅如此,即便在實際的建設過程中,也存在了很多問題。“既然要建遺址公園,那麼就必須要進行前期的考古科研工作——萬一地下有好東西被破壞了咋辦?”杜金鵬說。但問題是,遺址公園的建設是有工期時限的,如果要按期建設,考古工作就必須如期完成,而實際的考古工作進展是非常緩慢的。以大明宮遺址為例,建國以來,考古人員歷經數十年,不過才開挖了一萬平方米左右的面積。但為了趕建設與開放的工期,大明宮遺址公園建設之前的考古工作按照每年近萬平方米的速度在推進。同時,原本承諾的20多人考古隊伍,最終只有3人在場,這已經嚴重違背了考古工作的規律。科研變成了工程。“隋唐洛陽城從2007年開始,每年發掘一萬多平方米,但是正式工作人員就兩個。而這個地方,是隋唐到北宋宮殿的建築基址。作為一個宮殿考古工作者,最讓人撓頭的是宮殿建築基址找不清線索,尤其是隋唐到北宋,在同一個地方建宮殿,反復拆反復建,要想弄清楚相當困難。這種速度的發掘,不敢想象。”杜金鵬說。
更為諷刺的是,雖然號稱考古遺址公園,但目前的現狀是,一旦開園,考古工作就沒法進行了。“大明宮的遺址公園,除了展示區域,其它地方一律硬化,把考古工作拒之門外。即便有的遺址公園仍然存在開挖條件,但往往會被園方拒絕——開挖了就沒法走游人了。”杜金鵬說。
除此之外,一些設計方面的問題也耐人尋味。“我們在河南一個遺址公園評估時發現,原本那裡只需要用夯土堆一個台基就行,其實就是個小土堆,花不了幾個錢。但是建設的設計方卻使用了大量的鋼管水泥,建設了一個能跑火車的台基,不僅讓人氣憤,而且完全是種浪費。”杜金鵬說,“但實際上,設計方的薪資是按照工程造價的比例來算的,如果堆個土堆,那他們可能就沒幾毛錢收入,如果都用貴重東西,那他們就能獲得很多薪酬。”
如果放任不如不做
雖然有好的一面,但若放任公園建設中對遺址的破壞,文化遺產前景堪憂“在文物的保護利用方面,長期以來都有兩種聲音。有的認為利用文物就意味著對於考古的‘背叛’,有的則認為適當的利用是必要的。”杜金鵬說,“從長遠來看,我認為還是需要把文物利用起來。”
以城鄉建設與考古這對看似矛盾的兩方面來看,遺址公園的建設一定程度上是會推動城鄉建設的。“過去,我們是很煩城鄉建設的,因為一開挖蓋房,很有可能就挖到了古跡遺址。每個地方都在大搞建設,我們就成天疲於奔命。而且這種建設,往往都是大型機械,一鏟子下去,不知道破壞了多少好東西。”杜金鵬說。
但是遺址公園的建設則一定程度上調和了這種矛盾。以西安大明宮遺址公園為例,在這之前,那裡是有名的棚戶區,歷朝歷代從河南逃荒的人都在那裡落腳,可以想象,那裡談不上什麼基礎設施。後來,以國家名義建設遺址公園,讓出了那一片棚戶區,讓那裡的居民在別的地方過上了更體面的生活,對於城市發展來講是有好處的。
再比如,隋唐洛陽城遺址公園的建設,把著名的洛陽拖拉機廠和造紙廠遷了出去,甚至連洛陽的道路體系都因此改變,洛陽面貌為之一新。
在杜金鵬看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何把好事辦好,從評估結果來看,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想的是給這些遺址公園進行等級劃分。但是評估完了之後發現,這裡面問題很多,誰也不敢打分、分級了。”杜金鵬說。
杜金鵬認為,目前的評估更多著眼於公園的服務方面,缺乏全面的客觀標准。“既然叫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那麼就應該從名字本身入手。”杜金鵬說:“國家”就是要以政府投入為主導,管理層面定性也要以政府行為為主;“考古”則與科研工作掛鉤,即公園無論前期建設還是後期的開放,考古工作都應該能夠一直貫穿,就像秦陵兵馬俑一樣;“遺址”要傾向於保護,不能建設完了沒人管;“公園”則是展示與利用,做到讓游客游憩的同時,切實感受和學習到相關的知識。“如果國家的資金就是像撒胡椒面一樣給全國的大遺址都投錢,那還不如集中力量一年做好一個。不然的話,如果放任某些問題發展,那麼遺址公園的建設實際上破壞性要遠大於保護,那還不如不建。”杜金鵬說。
(來源:山東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