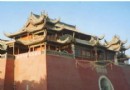山西介休太和巖牌樓
日期:2016/12/14 12:41:52 編輯:古代建築有哪些
介休位於山西省中南部,太丘山北側,汾河南畔,屬晉中市,距省會太原市139公裡。介休歷史悠久,最早見於史籍記載為周代魯隱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因出了春秋時期割股奉君的介子推、東漢時期博通典籍的郭林宗和北宋時期出將入相五十載的文彥博三位賢士名達,素有“三賢故裡”之稱。公元前636年,晉文公返國賞隨臣,介子推不言錄,與母隱居綿山。晉文公焚林求賢,子推竟與母抱樹而死,介休即依介子推休於此而得名。自公元前514年起,介休歷史上先後東部建置邬縣,西部建置平周邑,秦始皇設郡縣建置界休,以後改為界美、介休、平昌。東魏時,定陽郡一度僑治境內,北周時期,曾設置介休郡,隋、唐時期一度設介休郡、介州,鄰縣靈石公元590年建縣前,一直為介休地域,孝義歷史上曾幾度並入介休縣,宋、元、明、清時期,介休縣域和領屬關系基本保持不變。
歷史上的介休,為太原、河東、西河三郡的交叉地帶,是溝通三晉南北及陝西北部的交通樞紐,商業興隆,經濟發達,是山西有名的富庶之鄉。師延齡在《介休琉璃藝術》一文介紹,“介休東南的丘陵地區,不僅有豐富的森林煤炭資源,而且伴生有燒制陶瓷的必備原料柑泥,從而使琉璃的制作生產成為可能。介休的琉璃制作歷史可謂源遠流長。1979年在洪山鎮唐宋古窯址的南面丘陵上,出土了《大唐貞元十一年法興寺界限碑》,碑為雙面刻,背面又刻有《天會十四年洪山寺重修佛殿記》,“天會”為五代北漢劉繼元的年號。兩碑相距175年,但引人注目的是兩碑的碑文中都有“琉璃”二字。《法興寺界限碑》中有“西至琉璃寺,北至石佛腳”之句;《洪山寺重修佛殿記》中有“椽鋪玳瑁,瓦秋琉璃”的記載。表明在重修的洪山寺佛殿木椽的前面已用上了質如“玳瑁”的琉璃獸面,並在屋頂上裝飾了琉璃。以此印證《法興寺界限碑》中的“琉璃寺”也應該是一處用琉璃裝飾寺內屋頂的建築。山西省博物館現藏有北魏時期的綠釉菩薩,據說為抗戰前修築同蒲鐵路時於介休地段出土的。根據上述材料分析,介休極可能在隋唐,甚至北魏時期已經開始琉璃燒造的歷史。”宋元時期,介休琉璃工藝仍然相當發達,創燒於北宋初年的洪山古瓷窯和位於介休城內的元代瓷窯,都從側面證明了宋元時期介休琉璃工藝的發展。明清時期,介休琉璃的發展到了頂峰,位於介休洪山源神廟內的清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的《公同義阖碗窯行公議規條碑記》所載,“十三議:陽城黑貨琉璃貨等,不管幾人做工,酬神演戲派錢一吊文。”這說明琉璃技術已不是少數人的秘密,而是整個洪山碗行的人員都可以制作。《介休琉璃藝術》分析,“到了明朝,介休地區的琉璃燒造已達到極盛,遺留下來許多優秀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有空王殿、城陛廟和廣濟寺。清代介休地區的琉璃建築遺存,無論從規模和數量上均遠遠超過明代,且多宏觀巨制。規模最大,顏色造型也最復雜的,首推介休城內後土廟道教建築群。”除了後土廟外,介休城內草市巷的五岳廟,順城關的三結義廟,距城區2.5公裡的宋古鄉韓屯村的關帝廟,西段屯村夫子廟,都是琉璃建築的典范。另外,距城區東南7.5公裡的洪山鎮,有許多清代琉璃建築。介休城西南7.5公裡的小靳村東的東岳廟,也是琉璃建築的上乘之作。
郭華瞻在《介休琉璃》一文中論述了介休琉璃匠人的傳承,“元代有張元村張琳,張詳父子二人。明代匠師頗多,計有22人,以侯、王、秦、喬四姓為主。其中喬姓是明永樂年間自洪洞縣公孫村喬家由大槐樹遷來介休義常裡的,歷明成化、嘉靖、萬歷諸朝傳承不辍,可謂琉璃世家。”明代琉璃匠師開始外遷,主要遷居地是遼寧海城缸窯嶺侯氏,“明萬歷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自介休賈村移來,至清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始設琉璃窯承燒沈陽故宮大政殿,以及昭陵、福陵、永陵等各處琉璃。”
介休琉璃作品特點鮮明。首先,是種類繁多。《介休琉璃》一文將介休現存的琉璃建築分為八大類型:(1)吻獸,包括正吻、垂獸、套獸、戗獸,以城內後土廟所施為主要代表;(2)脊剎,以城內後土廟、城隍廟、五岳廟以及張壁空王祠所施為主要代表;(3)脊飾,城內後土廟、五岳廟、城隍廟以及張壁空王祠所施均較出色;(4)搏風及懸魚惹草,以城內後土廟三清獻樓、太寧宮,城隍廟正殿以及韓屯關帝廟所施最為精美;(5)嫔伽,見於城內後土廟鐘鼓樓、城隍廟正殿以及五岳廟獻亭、西段屯真武廟正殿;(6)影壁芯,城內後土廟三清獻樓八字影壁、三清觀山門影壁、太寧寺山門影壁等處所施最為典型;(7)匾、楹聯、雀替、彩畫、斗拱及拱眼壁,均見於北辛武琉璃坊。(8)碑,為國內目前所僅存,共兩塊。存於張壁空王祠前廊下,分別為明萬歷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造和明萬歷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造。其次,是題材廣泛,仙禽瑞獸、奇花異草等傳統祥瑞圖案以外,道教“八寶”、“暗八仙”等題材也豐富多樣,綿山勝境、汾水汪洋等地方景色也不少見。第三,色彩格調明快,不同於北京故宮為代表的官方琉璃建築,而注重色彩搭配,以黃、綠色為主,並使用孔雀藍色。作品立體感強,有的還使用了暈染法,更加生動傳神。
推薦閱讀:
山西介休五岳廟
山西代縣縣城邊靖樓
山西霍州娲皇廟
山西陵川吉祥寺

據《介休琉璃藝術》一文記載,“介休城西北20公裡的北辛武村保存有一處琉璃牌坊,其原為真武廟中軸線上的建築小品。牌坊面闊三間,四柱三樓,其下為高一米的石雕基座,樓為單檐歇山頂,仿、柱、椽、檩均為木結構,斗拱為琉璃品。立柱外用磚實砌成1x1米的方柱,外貼以素孔雀藍貼面夕中嵌琉璃燒成的對聯,普拍枋闌額上亦飾以透雕的琉璃貼面,透雕的琉璃彎形雀替形成三個券形拱門,顯得分外秀雅。門上的匾亦均為琉璃制品。整個牌坊富麗堂皇,更襯托出真武廟當年的顯赫神聖。在中門右邊方柱下端有“光緒丁酉年造”的題記,據傳真武廟所用琉璃匠人都是從太原等地調來的高手。”北辛武村很好找,但是問了幾個人都不知到村裡的牌樓在哪裡。好在尋訪之前看了國保的博客,知道太和巖牌樓在該村的幼兒園內,改問幼兒園在哪裡,很順利的就找到了。
據傳,太和巖牌樓為北辛武村晉商巨富冀氏家族在對村內的廟宇進行補修時,在真武廟中軸線之山門前所新建,雖然現在只剩下了牌樓這個單體建築,但是由此可以想象當年真武廟的氣勢。冀氏家族現在泯沒無聞,但是在200年前,是天下聞名的富商大賈。王進在《解密晉商文化》一書中說,“清代初年,擁有千萬兩家財的大戶人家,中國只有兩家,叫做南季北亢。南方是季家,北方是山西臨汾亢家。亢家擁有千萬兩以上的白銀,在揚州沿大運河建有十幾裡的私家花園,這是在千萬兩以上的晉商。擁有八百萬兩白銀以上的實力的晉商,有兩家。一個是介休的冀家,一個是介休的侯家。擁有五百萬兩白銀以上的家族,祁縣的喬家、渠家,榆次的王家和太谷縣的曹家。這些數字表達出一個什麼概念呢?拿清代乾隆三十五年國家財政相比,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的時候,國家財政收入是三千五百萬兩白銀,也就是說,晉商三到五家財富的總和就和國家財政收入當。”可見,現在大家津津樂道的王家,渠家,喬家和曹家,在當年,實力都不如介休北辛武村的冀家。
張正明所著《晉商興衰史》,對冀氏興衰進行了描述,“冀氏是宋代從山西臨晉縣遷入介休縣邬城,後又遷入介休北辛武村。冀氏是大戶,其“支派分出,丁口益眾,梓裡相逢,每難識別,兼以宦游遠省者有人,服賈他鄉者有人,又遷廣平、遷湖北、遷陝西、遷北口”。冀氏約在乾隆時開始發跡,到冀氏十七世冀國定時期,冀氏商業已相當可觀。《清稗類鈔》稱介休冀氏有資產銀30萬兩。道光初,冀氏在湖北樊城、襄陽等地的商鋪有7O多家,經營以當鋪為主,次為油房、雜貨鋪,其中資本在10萬兩以上的商號有鐘盛、增盛、世盛、恆盛、永盛當鋪和平遙謙盛亨布莊。這時,冀氏有資產達300萬銀兩。但冀氏富後不願露富,冀國定為掩飾其富,有對聯雲:處世無才惟守拙,容身有地不求寬。冀國定是冀氏單傳,到國定年逾40歲時,又膝下無子,遂繼娶四房馬太夫人,後生以公等五子。國定去世後,因“諸子未更事”,內外造事皆由馬太夫人經理。她“不出戶庭,而大辔在手,綜理精密”,絲毫不比國定遜色,據說平遙縣開標利,如馬太夫人不到,就開不了,因為不知她是放還是收。其經營才干由此可見。。據清人徐繼畲《冀母馬太夫人七十壽》載:“太夫人為诰贈資政大夫一齋冀公之繼室,母家簪纓世胄,夙娴詩禮,贈公自祖父以上單傳者七世,家稱富有,而苦於襄助無人,自太夫人來歸,乃准母家儀式相之,以立家規,贈公資業半在荊楚,又有在京師畿輔山左者,往來照料,井井有條,而家政則一委之太夫人。贈公自奉儉約,兩歲恆雜粗粝。太夫人曰:此惜福之道也。然自奉宜薄,待人不厭其厚。即擅素封之名義,所當為不宜居人後。贈公深以為然,故指囤贈舟之事,不一而足。會垣修貢院,首捐萬金,族戚鄰裡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贈助成之。贈公既逝,太夫人以諸於未更事,內外諸事悉自經理。南北貿易經商字號凡數十處,伙歸呈單薄稍有罅漏,即為指出,無不咋舌駭服。不出戶庭,而大辔在手。綜理精密,不減贈公在時。又待伙極厚,故人皆樂為盡力。……太夫人男子五,有己出,有庶出,撫之如一,教文如一。諸子雖得高爵,而躬躬修敕不敢以裘馬耀鄉闾,供客極豐腆,而家中兩餐仍儉素。曰:惜福則福自長也。故諸子生富家而能飽粗粝。”大約在鹹豐六七年間,馬大夫人曾為五個兒子分家各立門戶,從此冀家有“五信堂”之稱。冀氏所經營的商業,除平遙謙盛亨布莊(後改為票號)歸五堂共有外,其余均分給各門,加上他們在分家後又新設的商號,各門的情況是:以公(悅信堂):析產分到增盛、廣盛當鋪,之後在直隸大名府又設當鋪、顏料莊數家,在介休張蘭鎮設悅盛昌、悅來號錢莊,又在湖北通過當鋪放帳兼並了部分土地。以廉(笃信堂):析產分到鐘盛、益盛當鋪,後在介休張蘭鎮又設謙盛晉錢莊、平遙縣寶興成綢緞莊。以中(立信堂):析產分到恆盛、文盛當鋪,後在介休張蘭鎮又設恆盛茂商號。以和(敦信堂):析產分到永盛、星盛當鋪,後在湖北樊城又設鼎順、永順二當鋪,在北京設仁盛當鋪,在庫倫(烏蘭巴托)、喇嘛廟和張家口等地設恆順發等皮毛商號,又在介休萬戶堡購買土地二頃多,在洪山購買水地一頃多。以正(有容堂):因同馬太夫人在一起,析產只分到世盛當鋪,另有現銀10萬兩,後在祁縣設天聚和茶莊。以正是秀才,據說為考舉方便,在平遙設其德昌票號(兼營布匹),在太原設其昌水綢緞莊,在晉祠設其世昌、其昌泰雜貨莊,號稱“四桿旗(其)”,並在晉祠購稻田四頃。“五倍堂”除在外地購買土地外,在原籍本村共有土地30多頃,占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光緒初年,以廉、以中各以銀30萬兩建大宅院,以正用銀10余萬兩購北辛武村破產財主“閻百萬”房捨,以和用銀10多萬兩新建房捨和花園,只有以正留住原宅。冀氏房室裝滿富麗堂皇,十分講究,又在北辛武村開設雜貨、肉、藥、當鋪,以方便其生活需要。冀氏十九世靈哥是冀氏家族中的纨绔子弟。前述介休民間流傳的說法:“介休有個三不管,侯奎靈哥二大王。”靈哥是冀以公的長子,名惟聰,靈哥是乳名。他自幼嬌生慣養,長大後奢侈浪費,揮金如土。介休縣張蘭鎮逢農歷九月二十日有廟會,靈哥與介體二大王(郭可觀)各養一戲班,比賽哪個戲班的戲演得好。靈哥又與北賈村侯奎比賽跑馬車,壓死人後,行賄地方官吏,竟逍遙法外。冀氏商業從鹹豐時起已因戰爭遭受損失。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冀氏“商號之遭兵燹十余家,資已去大半”。馬太夫人從湘南兩湖調回山西現銀五六十萬,資本向北方轉移,並在天津設立當鋪。這時“晉省捐輸之議亦起”,冀氏“接連六七次,計前後捐輸凡數十萬金。”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冀氏在北京的“海澱字號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隸諸字號資本亦大半被焚掠,較之以前家資不及十之二三”。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庚子事變,冀氏在天津、北京的當鋪被搶掠燒毀,平遙縣、介休縣張蘭鎮的謙盛亨票號、謙盛錢莊發生倒賬,損失銀150萬兩,冀氏商業從此衰敗。冀氏到光緒時,人丁稀缺,庚子事變前“五信堂”只有冀以和一人在世。庚子事變後,男子只有惟清,女性只有惟聰小女兒馬奶子在世。冀氏商業衰落後,由他倆代表各處清理債務。他倆又邀請張蘭鎮賈退安協助。並公告大家稱:“庚子年後,民家生意,四處損失,無法清理。協同債權,邀請張蘭賈退安先生。破產還債,以清各處財源。止利歸本,分期歸還。”
冀以和是太和巖牌樓的建造人。據《冀氏之輝煌山西介休北辛武冀家》一文介紹,冀以和(公元1831年至公元1900年),字達堂,號藹一,山西省介休市北辛武村人,以和系第十八世主東,是使冀家商業資本發展到鼎盛時期,而又瀕臨徹底衰亡的一個關鍵人物。冀以和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他的父親於道光十八年(公元1828年)去世時。家財由其母馬氏掌管到鹹豐初年(公元1851年)才主持弟兄們分了家,但開設在平遙縣的乾盛亨布莊、介休張蘭鎮的乾盛晉錢莊、祁縣城的天全茶莊以及這幾個商號分設在全國各地的分莊沒有分開,仍由弟兄們合伙經營。當時冀以和年僅20多歲,但卻最為精明能干,善於結交朋友,理財之術尤勝諸兄。因此,便成為冀氏合伙經營商業的主東,在其主持下不到幾年,果然使商業資本又有了新的發展。他看到當時已經盛行的山西票號盈利甚巨,覺得開辦票號營業有利可圖,於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便將乾盛亨布莊改為票號,專營匯兌和存款放款業務,總號設在平遙縣城內,並在北京、天津、漢口、上海、西安、昆明等大城市及四川、河南、山東、湖南等省設立分莊。為了便於組織和指揮貿易、金融活動,他本人常住北京分莊坐鎮,並在北京設立公館,大結京城和各地豪商巨戶和清政府一些大官僚,以作為票號發展的支柱。因此,在很短時間內,錢莊票號的匯兌存款、放款業務便大大活躍起來,其他商業貿易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為了提高他的聲譽,更好地開展商業金融活動,他也深知坐官為宦的重要。因此,雖然他這個秀才也沒有中過,但通過與大官僚們的交往,花了些銀兩,捐了個官銜,為軍功議敘府參將,軍功議敘知府一品,封殿榮祿大夫賞戴花翎候選道台。這個官銜雖非實職,但憑著它更加強了他的活動能量,對獲取巨額利潤聚斂大量資財更為有利。因此,在同治末期,光緒前期,冀家商業資本便發展到鼎盛時期。特別是錢莊票號業務,幾乎“匯通天下”。但是,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步步深入,清政府逐漸走向腐敗沒落,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商業也面臨著種種危機。光緒八九年間(公元1882-1883年),乾盛亨票號首先遭到一件公案的影響,幾致倒閉。這件公案是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攬雲南報銷,伙同雲南幾個官員侵用公款,將款匯至京城取用;而乾盛亨票號雲南和北京分莊,正是這筆錢的過局,使其聲譽大損,再加上當時其他票號有的也發生類似案件,冀以和預感到前景發發可危,於光緒十一二年間(公元1885—1886年),對票號進行收束。但因存放款涉及到好多官僚大戶,存款要取走,放款收不回,最後決定把外欠款欠在平遙總號賬上,欠外款20多萬兩銀子都在平遙總號提取。但總號沒有那麼多銀兩支付,一時間形成擠兌,於是派人到北辛武村找東家冀以和,冀以和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只得告來人派車到北辛武村家裡拉銀子還債。第二天平遙總號派了5輛大車在北辛武村拉了一天元寶。這件事轟動了平遙城,人們都說乾盛亨冀東家開了銀庫了。波動後各地又繼續經營下去,但其營業卻不如前,同時,冀以和本人也進入老年,年輕時的銳氣已減,精力逐漸轉移在家鄉興建住宅等方面,商務金融活動多由各商號經理經辦,本人漸少過問。待家鄉住宅及園林落成後,住進了新居,盡情安樂。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三月,是冀以和的七十壽誕,他所經營的全國各地商號及遠近大小官僚前來為其祝壽,其樂無窮,但這已是冀家表面繁榮和回光返照走向沒落年月之時。壽事過後不久,興盡悲來,冀以和病臥床頭,病情逐日加重,六月初二去世。而冀氏各地的商號也於當年的八月開始,在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社會大亂中,有的商號被燒之一光,有的被搶劫一空,失落的不可言狀,最後在眾多存款戶的逼迫下,冀氏傾家蕩產,還清了債務,走向沒落。冀以和年老歸裡後,在地方建設方面有所建樹,曾在其家花園開辦私塾,名“登瀛文社”,招收秀才免費入學,深造培訓了一些人才;並把北辛武村裡的7座廟宇進行了補修,落了個“樂善好施”的名聲。最突出的是補修真武廟時,在院中軸線上的琉璃牌坊,氣勢雄偉,色彩絢麗,工藝精巧,集介休當時名產琉璃燒造藝術於一身,至今猶存,就是太和巖牌樓。
太和巖牌樓的建造年代,資料多稱牌樓上有“光緒丁酉年造”的題記,為冀以和於1897年所新建。然冀廣大所著《山西介休北辛武冀氏經商年記》一文稱,“乾隆42年(公元1777年),冀之瑜(15世)出白銀2萬兩,帶頭在北辛武村修建真武廟和修繕沙河橋。道光14年至道光18年(公元1834年至公元1838年),以冀國定為首在北辛武村修建琉璃戲台和琉璃牌樓各一座,總耗資12萬兩白銀,冀國定一人出資10萬兩。光緒5年至光緒15年(公元1879年至1889年),冀以和帶領冀氏家族重修繕北辛武13座祠廟,耗資60萬兩白銀。”文中只提到了道光年間冀國定所造琉璃牌樓,沒有提及光緒年間冀以和所建琉璃牌樓。目前的太和巖牌樓,是冀國定先造,冀以和補修,還是由冀以和新造,似已很難考證。
推薦閱讀:
山西介休五岳廟
山西代縣縣城邊靖樓
山西霍州娲皇廟
山西陵川吉祥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