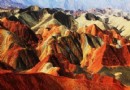仁本堂磚雕賞析
日期:2016/12/15 1:22:23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雕刻是一門手工藝。是手工技術,當然要用手,用力,用技;是手工的藝術,則更要用智,用情,用心。因此,每一幅雕刻作品,都有手的溫度,力的印痕,技的精妙,更有人的智慧,情的化育,心的靈性。
有話說:“無雕不成屋,有刻斯為貴。 ”
中國古典建築的雕刻,是詩的抒寫,畫的素繪,是文化的吐納,東方意象的精神高揚。
歷史青睐藝術,藝術鐘情文心。文心雕龍,是歷史之戀,也是藝術之魅。有的雕刻是手藝,手藝之品在匠心,匠而無心則沒有文心的照眼,便面目死板,匠氣十足,歷史就會無情地侵蝕它的形象;雕刻,一旦得匠心的眷顧,便藝味盎然,生氣遠出,歷史即慨然賜之以時間的生命,抖落出來,分明是蓄養天地之心和人文精神的天工圖畫。
仁本堂石雕不顯,磚雕則疏朗有致,鑲嵌於門樓門楣、粉牆照壁、樓腰裙板以及庭院之中,游觀之際,目之所遇,只覺匠心纖運,慧照耀眼。做為門樓或者照壁磚雕,或為建築點題、傳神,或表主人心態、情趣,一一透出和易而靜穆的文化性格,恰與主人的內心世界默契無間。黑格爾說得好:建築,我們也可以把它比作書頁,雖然局限在一定的空間裡,卻像鐘聲一樣能喚起心靈深處的幽情和遐想。一幀幀磚雕作品與建築融為一體,其所刻警句格言、神話傳說、歷史典故、花鳥魚蟲等等,無一不是“詩意”和“畫意”之外的“建築意”。建築意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兩位建築學家提出來的。簡而言之,是指建築與人,建築與自然、建築與社會、建築與人文,以及與時代和歷史之間達成和諧的文化意蘊和美感。
中國典型的古典建築,一般於廳堂之間建有門樓。門樓的功能一在實用,即為廳堂之間的進出口;二在審美,是古典裝飾性建築;三在為宅院“點題”,以表主人心中憧憬;四在表現主人的情趣愛好,以顯示自己的文化品性。
如用黑格爾所喻,建築是一本書,那麼,仁本堂則是一本古典線裝書。磚雕門樓可謂書的扉頁。磚雕匾額即為書的題簽,是主題的呈示,是建築意的畫龍點睛。匾額題曰:禮為教本,取《顏氏家訓》中語,其意正與“仁本”相合。以禮治家,垂訓後人,奉儒教化,盡在望中。
儒家以禮教為治世之本,所謂“克己復禮”,旨在行大道仁政而循循有矩,不致僭越逾矩。據有學者考證,“儒”之本義源於祭祀儀禮。“儒”與“禮”,具有同義復合的意味。當然,孔子生時以及後世接踵而出的種種儒家學說,自有歷史的局限,良莠羼雜,難免寓迷信或王權的宗教意識和統治思想。孔子所誡君民“齊之以禮”的“禮”,意即凡禮儀禮制、名位等級、官階品位、制度品節、社會規范、道德准則……總之,一切社會行為,悉合禮數,才能君以使人國泰民安。這與今日所倡之“禮”,自有天壤之別,豈可相提並論定於一是?然而,禮,一經哲學的抽象,單取隱喻或引申的意義,禮,則表現為一種秩序,一種內蘊自然與人和社會與人的生命節律。所謂“禮者天地之序”,“大禮與天地同節。 ”(《禮記·樂記》)而“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禮論》)因此,我們只要賦予“禮”以現代文明的內核,反映現代社會與時俱進的規范和法度,契合自然生態與人的精神生態共時性的協調發展,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讓“歷史中的人”走出來,而與今人同構“禮”的文化精魂呢?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 ”(《論語·季氏》)其學“禮”而立,旨在行禮禀德。德之高者,是為仁。這又回到仁本堂內蘊的文化主題和意義上來了。
一宅之建門樓崇偉,偌大一個家便顯出氣派來。一如明代計成所說:“象城堞有樓,以壯觀也。”(《園冶·屋宇》)仁本堂的門樓不是顯富而主在表達,表達的是主人的胸襟氣度。正中一額,猶若深邃的眼睛,流露出來的是以禮教自持、又以禮教傳家的心中希冀,可見主人品位不俗,自顯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匾額揮毫者,必與主人親近或心儀,書體藝品則又為主人喜歡或推崇。看來主人尤喜隸書,“禮為教本”四字,著墨浮雕,結體方正而排疊舒展,筆勢波詭而又沉靜莊重,書者運筆於楷隸之間,尤其一“本”字,木下一橫竟以反向半圓結體收筆,破格落墨則又隱含秦篆余意,正所謂“方有圓之象”,益顯含蓄蘊藉。落款者蔣元益,字希元,號漢卿,長洲人,乾隆十年(1745)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觀其書風,自是莊重也灑然,與仁本堂建築的“言明義之所”(唐·蘇鹗:《蘇錄·工段營造錄》)的文化內涵相吻合,與其淡定靜穆的風格倒也珠聯璧合,熠熠生輝。
仁本堂門樓的磚雕裝飾,不事秾麗繁復,而以簡靜雅致擅勝,有類明代風格。枋間排科簡飾花卉圖案,磚雕掛落以透雕紋飾,匾額則以雲紋框邊,兩邊對稱嵌“仁貴救駕”和“文王訪賢”典故磚雕圖像各一,額下又為一“三顧茅廬”磚雕圖像,兩邊以水紋樣寬幅飾邊,如一畫橫批,以求上下左右勻稱平衡。仰望之際,只覺造型古樸,刀法圓潤,層次分明而細膩,線條流暢而古秀,恰恰體現了江南民居的水鄉風情。
古建築學家張馭寰說:“清代流行在合院大宅裡、二道門的牆壁上,或院內牆壁內外懸掛匾聯,以治國齊家、教子讀書、尊禮等方面的文章段落居多,做成磚刻或石刻鑲於牆面上,使在院中的人隨時欣賞、觀摩,給家人子孫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文字也因有了裝飾的意義,溫文爾雅,別有風味,體現出一種詩書門第光宗耀祖的思想。 ”(《中國古建築裝飾講座》第50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版)建於清代的仁本堂,不能不受時代的影響,有的院落,把磚刻匾額鑲嵌於粉牆,匾額的形制、框邊花紋以及所刻文字,一則以與花木假山相與映襯而起裝飾作用,再則以所書文字內容體現出“詩書傳家久,禮儀振家風”的殷切期望和書卷氣息。
東花廳院中南牆,有一磚額題曰:“采煥尊彝”,亦為隸體。前者之門樓“禮為教本”四字,緊密精謹,整饬停勻,輕靈波揚,漪瀾成文,秀逸沖融有謙謙君子風;而此院中“采煥尊彝”四字,則筆重墨飽,左右開張,波磔尤為誇張,一波三折,猶見波浪湧動之勢,頓筆外拓,更具駿發滿足之態,神韻翩然有曠曠雅士姿。真可贊歎者,還在刻工精妙,匠心入情,雖為雕刻,卻墨意淋漓。磚額上款署“鹹豐乙卯秋桂上浣”,乙卯當是鹹豐五年即1855年,許是新宅落成時。下款署書家名,只因風蝕雨侵字跡不清,一時難以辨識,真是可惜了去。
磚額內容亦可資雅玩。尊和彝,為行禮儀時所用酒具,在古代皆屬禮器。采煥尊彝,說是文采煥發的酒器,顯然直白得毫無意思。有說主人立額意在發揚淳和家風,以期世代平安富貴,可得永年,似也含混其義,難能心頤。為此我特請教文藝美學家金學智先生,承蒙指點迷津,說,采煥尊彝,也即尊彝采煥,行禮之器光彩煥發之謂,必也含隱喻之意。我因之忽生感悟,心境豁然開朗,這與門樓額文相互映發,首以禮之教寄主人心中之願,繼以得禮樂之和而文采灼灼,煥然生輝,又寓家道源遠流長,光彩照人。一前一後,一因一果,守“本”揚禮,花開並蒂,好一番詩書人家的禮樂相和的好光景。
與磚雕匾額相映相襯的是一竹一樹一石。石是太湖石,高可兩米余,石姿峰態殚奇盡怪,皺瘦漏透窈窕愉目,其種種美致,自古以來,早有定評。然而這出自太湖的原石,置於此院,便有了堅守本土的悠長意味。湖島,湖樓,湖石,皆被太湖攬在懷中,俯仰水天一色,呼吸晨昏湖味,不時漫出一種浸潤肺腑的美感靈動。所見歷歷,一如畫本,這真可與鄭板橋《竹石圖》的深遠意境相媲美了。
湖石之背,素壁一隅,有方竹一叢。竹的品種多為圓竹,余則有扁竹、方竹、三角竹等,皆屬稀有竹品。有說方竹不祥,愛竹者卻並不忌諱,喜的是竹影扶疏透日,篩月梳風,虛心抱節而素守平生,冷翠潇遠又堅貞摯著,其象征意蘊自可深味不盡。
再有可貴者,是依石而生的一株五色山茶。200余年的樹齡,本已令人贊歎,冬春之際花開五色,更叫人刮目相看。但見花樹婉立庭院,枝葉繁盛高過層樓。花開之時,樹頭枝間,萬朵花蕾經月含苞,一朝怒放,燦然冷艷。紅的是火,白的是雪,粉的是胭,黃的是脂,間或見雜色花紋缤紛絢麗。想起明代詩人於若瀛《山茶》詩雲:“既足風前態,還宜雪裡嬌”。最是花事“采煥”時,兼有“尊彝”可把酒花前,看來主人“艷福”匪淺,斐然醉色,真正令我等匆匆行客心生嫉妒,愛煞羨煞。
主人貪心不足,於東花廳院中賞花品竹余興未盡,又於西花廳南牆嵌一磚額,額文為:“花竹怡情”。看來主人不是俨然夫子,風晨月夕時與自然親,與天地和。東花廳西花廳,東也花竹西也花竹,一院一“采煥”,一院一“怡情”。不必問花是何花竹是何品,不必問世間何事人生何憂,只看取綠葉婆娑嫣然搖動,只消得嬌姿嘉艷天然窈窕。無事是福,閒處是樂。酡醉花間最好不要驚醒,竹蔭徜徉最好是省得自家品性。這就是生活,這就是人生。主人真懂得享受,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享受,是一種心情,一種體驗。
是的,花竹怡情。書體為行楷,點劃自然,落筆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似脈承東坡筆意。額文镂空陰刻,刀與筆鋒鋒如一,沉靜雅正中寓妍姿美態,空靈飄逸裡卻見骨氣勁健。寫得好,刻得也好,相得益彰,為西院增色。上款署年“鹹豐乙卯盛夏”,可知斯額寫於東院“采煥”同年,時在“盛夏”而先於“桂秋”。可惜書者落款處被翠竹繁枝密葉所掩,未能看清,想來不是俗人。匾額邊框為高浮雕磚刻,並輔以透雕工藝,有瑞獸、花卉等圖形,凸凹分明,造型生動,種種形象令人驚異,其強烈的文化蘊涵和裝飾意味,足資賞玩體味神怡。
仁本堂磚雕寥寥,然幅幅皆精雕細琢,工藝超拔,歷史典故瑞獸嘉卉等形制類秦漢畫像磚,多采用浮雕、透雕、镂雕、半圓雕等雕刻工藝,刀法圓潤,結構嚴謹,層次分明,造型古樸,如“吉祥瑞獸”、“蘇武牧羊”種種題材,紋樣多為復制,在其他古建築中屢見不鮮。倒是其中兩塊,所刻寓意值得玩味。一是“觀音灑水”,一是“大禹治水”;一取神話,一取傳說。二幅磚刻,皆表現了江南水鄉人對“水”的文化認同和情感態度:一是對水的渴盼,也是對水的感恩;一是對水的敬畏,也是對水的制馭。在古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灑水”與“治水”,親水與畏水,是兩種對立的心理因素,而這兩塊磚刻,則藉兩則家喻戶曉的神話和傳說故事,在人的念祖情結和英雄崇拜的情感驅策下,辯證地統一起來了。
我不能不感佩水的題材選擇的哲學眼光,我又不能不佩服磚雕工匠用精湛的手藝,表達了吳地子民對水的神秘性的破譯。西山人的歷史,不就寫在水上,寫在太湖上嗎?堂裡人的人生足跡,不也印在水上,印在太湖上嗎?湖風拂過,山雨洗過。時間隨風而逝,往事經雨飄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逝的是生命,不散的是精神。
其實,磚雕藝術給予人的,是歷史的感悟和人文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