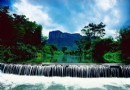南京近現代建築有望納入保護_中國文物網-文博收藏藝術專業門戶網
日期:2016/12/14 21:29:33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南京悠久的歷史文化,注定了這座城市的特色是新舊文化交相輝映 CFP供圖
前不久,南京地鐵5號線因為沿途有183處文物點,涉及國家級文保單位3處;地鐵5號線的選線規劃設計上報國家文物局後,被國家文物局“暫否”,要求南京對所報“選線規劃設計方案”和“文物影響評估報告”進行補充和修改。南京的文保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是好事,體現了“城建為文保”讓步的觀念。
南京是歷史文化名城,地上地下,文化遺存多多。在一個舉國大開發大發展的年代,在南京,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保護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在某一個集中改造開發的階段,這種矛盾尤為突出。好在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觀念在變,也在不斷地進步。
城市需要日新月異,也需要文化品格和歷史內涵。
在南京,城建與文保最終從各執一詞,走向了協商與妥協。
現代快報記者
胡玉梅 徐萌 馬樂樂
上世紀80年代
南京第一次“摸”文化家底
朱自清曾經說:“逛南京像逛古董鋪子,到處都有些時代侵蝕的遺痕。你可以摩挲,可以憑吊,可以悠然遐想……”
1982年,南京被國務院公布為首批歷史文化名城。隨後,南京市、區開展聯動普查,查閱相關資料和座談,制定保護規劃。但是當時哪些是古董、是寶貝?人們的心裡還沒有譜。
1984年,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啟動,南京也開始了對文化家底的搜尋、普查工作。當時,原本是小學老師的楊新華,被借調到雨花台區做文物普查工作。“當時,雨花台區做文物普查的,就我和王梅影兩個。”王梅影年齡比較大,在外面跑的就是楊新華一人。當時的牛首山還比較荒,草叢一人多高,文物普查人員沒有定位儀、沒有手機,只有一個老舊照相機,楊新華每天帶著饅頭,背著一個破包,田野、山上到處跑,為雨花台區的文物建立“家譜”,之後,列入文保單位。
也就是1984年,南京出台了第一版名城保護規劃。南京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童本勤對現代快報記者介紹說,當時的名城保護規劃對南京的山水格局、歷史格局,以及其中的歷史文化資源,都確定了保護名錄,劃出了紫線保護范圍,“當時南京屬於全國第一批畫出紫線規劃的,而第一版保護規劃提出大南京概念,在全國也很出名。”
當時,公眾對於保護文化遺存並不太理解。童本勤說,人們覺得南京老房子多,不夠現代化,想在城市建高層建築,“新街口金陵飯店成為必游景點,人們都要去旋廳鳥瞰南京城,而老房子、老建築又老又舊,沒什麼用,我們想保還常常遇到困難。”
上世紀90年代
張府園南唐護龍河被毀
“上世紀80年代,南京城內的建設還不多。”南京大學教授蔣贊初回憶。但上世紀90年代開始,“建設”和“文保”這對兄弟,就遭遇上了。1990年前後,中山南路南下工程,首次打破了原來的老門西的格局……
1993年,66歲的蔣贊初退休,他和東南大學教授潘谷西、南京博物院原院長梁白泉三人形成了“三人文保小組”,為南京的文保鼓與呼。讓蔣贊初至今感到痛心的是,上世紀90年代,張府園改建住宅樓時,挖到了南唐時期的護龍河,但隨即被毀掉了。
“當時挖出來的護龍河有20余米長,寬三四米。當時我、潘先生和江蘇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員趕到現場,我一看,河兩邊護岸石頭和南唐二陵的一樣;而且這段護龍河在史料上有詳細介紹,我們都覺得成為省級文保單位不是問題。”蔣贊初回憶說,當時他們向有關領導建議,立即把這處護龍河升級為省級文保單位。潘谷西說,他本人免費為這處小區設計個亭子,讓這段護龍河變為小區綠地,可以供市民參觀、休閒。但是,施工單位連夜讓民工把石砌的護龍河駁岸起掉。第二天,蔣贊初他們再去時,對方說,“石頭已經取出來了,你們不是要石頭嗎?”後來,這裡又發現另一段南唐護龍河,但也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
“南唐是南京重要的一段歷史,但現在南唐的遺存,只有南唐二陵,主城區內沒有任何遺存,這讓我深感痛心。如果保留下來了,現在肯定是一處省級文保,還是一個旅游景點,多好。”蔣贊初搖搖頭。
2006年、2009年
南京響起“救救老城南”
20世紀初,南京舊城改造如火如荼,考古鏟跟在挖土機後面忙碌。“那時候,馬道街拆遷,因為房子特別好,每天都有上萬人圍觀。”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委員薛冰回憶。
讓公眾記憶最為深刻的還是:告別老城南事件。老城南是南京的根,從南唐始,歷經明清和民國,都沒有大的變化。老城南以中華路為界,中華路東為門東,中華路西邊叫門西。門東以代表科舉文化的貢院為中心,包括為它服務的書坊印刷業與商業娛樂等設施,也分布有一些手工業區和居民區。門西是以絲織業為中心的工商業區,也有一些居民區和寺廟。
“都說,甘家大院是南京99間半,其實老城南有不少99間半。”蔣贊初說,拆遷之前,顏料坊的山西會館,就堪稱99間半,但後來被拆掉了。“老門東也有99間半,別的不說,沈萬三故居就稱得上是。”到了2006年,在“打造一個新城南”與“利用拆遷費來拉動居民消費”的口號下,有關部門開始拆遷成片的老城街區,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拆遷門西地區秦淮河畔的傳統絲織業中心地點——顏料坊與牛市街區。“街區中,和雲錦有關的建築、雲章公所等都保存得很完好,但當時,我們趕到的時候,就連南京市級文保單位牛市64號清代建築也被拆字上牆了。”蔣贊初回憶。
2006年8月,16位國字號文保專家上書建設部、國家文物局,懇請停止拆遷;8月17日,快報記者陪同南京文博界二老蔣贊初、梁白泉,以及著名作家葉兆言來到顏料坊、牛市拆遷現場,作別老城南。之後,快報用8個版篇幅推出的“老城南”專題,打動了成千上萬南京人的心。
2009年6月,還是因為南京老城
南的拆遷改造,專家們又上書相關部門。由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組成的調查組隨後抵達南京,短短三天時間,向負責老城改造規劃的專家了解情況,與遞交呼吁書的專家學者座談,到老城南拆遷工地現場調查。三天緊張調查之後,調查組作出了立即停止甘熙故居周邊民居拆遷改造工程的決定。
2010年
南京向“大拆大建”告別
“近30年來,從對文保建築的保護拓展到對歷史街區和老城區整體的保護、從文物保護拓展到文化遺產保護,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拓展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伴隨名城保護進步的,是現代化進程中被喚醒的文化自覺。”
“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800美元—3000美元之間,城市面貌變化最大,文化遺產破壞最重;人均GDP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間,文化消費成為必需,保護文化遺產成為共識,但保護常常為建設讓路;”龔良介紹說:“一旦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人們會主動尋找文化遺產加以保護。”
城市改建和千年文脈傳承,在兩者的不斷碰撞中,局勢也悄悄發生著變化。“就拿地下文物來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洛陽已經有了地下文物管理條例,而南京的地下文物管理條例到1999年才出來,管理條例上規定,建設單位遇上文物要主動上報,進行考古發掘。”蔣贊初說。
一系列的文保條例,也在不斷出爐。2010年,《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下稱“新《條例》”)12月1日正式實施。南京大學學者姚遠認為,這是南京向“大拆大建”告別的標志性條例。姚遠說,南京市規劃局、市法制辦、市文物局等部門參與起草的新《條例》,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中三大關鍵性的變化,值得肯定。
“新《條例》在總則第三條確定了‘政府主導、統籌規劃、整體保護、合理利用’的保護原則,用法律的形式明確了‘政府主導’和‘整體保護’的指導地位。”姚遠表示,作為新《條例》的第一個實踐案例,《南京老城南歷史城區保護規劃與城市設計》方案,提出改變以往資金就地平衡、就區平衡的舊模式,由政府投資進行保護。
第二個變化是,新《條例》推動公眾參與,保護兼顧民生,這是保護手段之變。第三個變化是,變“先出讓,後考古”為“先考古,後出讓”,重視地下遺址保護。新《條例》第四十條提出“國土行政主管部門應當事先委托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對出讓或者劃撥地塊進行考古調查、勘探。”
“這一轉變意義太重大了。”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長楊新華說,“考古鏟追著推土機,折射出多年來的文物保護的困境。如今,考古部門可以在土地出讓前進行考古發掘,既有利於文物保護,也便於土地的後續規劃。”
2014年
公布1509處不可移動文物
過去,城市建設中,往往有的老建築被拆掉了,建設部門會說“我不知道它的歷史價值,不知道它是文物”。
2014年,[email protected]��南京11個區的不可移動文物,總計1509處。這些新公布的不可移動文物涉及方方面面,遍及南京各個角落。1968年建成通車的南京長江大橋、41歲的五台山體育館、31歲的金陵飯店……南京的文物保護步入了一個不以“年齡”大小為標准,只要有文化、藝術、歷史價值,就應保盡保的全面保護時代,也可以說是“大橋時代”。
1509處不可移動文物加上之前的南京市級、省級、國保級,南京的文保達到2300多處。南京市文廣新局一位負責人告訴現代快報記者,也許,公眾眼裡,就是知道了身邊又多了幾處文保,但對於文保來說意義非同小可,公
布為文保後,這1509處文物就被依法保護了,誰也不能拆它們。
與此同時,南京文廣新局聘請了一大批文物志願者,這些志願者走入田野、大街小巷,記錄南京文保的變化,如果發現毀壞文物現象,立刻上報給文物部門,讓南京市文化綜合執法大隊的工作人員可以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執法。
當下
“文化先行”
各路專家意見都一致了
“我10年前開始作為南京市規劃的專家成員,這10年來,深有感觸。”薛冰說,南京現在迎來了建設和文保的最好時機。
“早幾年,參加規劃會,每次都感覺很緊張,有時會感覺很無奈。有的規劃專家論證會上,因為出於憤怒,會頂牛起來。”薛冰說,每次規劃會上,參加會議的有建設、交通、環保、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學者,每個專家的發言,最終都要形成文字,專家要在上面簽字。以前,專家們的意見會出現非常大的不同,而現在,不管是建設、交通還是環保,大家的意見都很一致:文化先行。
“前天,我剛參加了有關下關大馬路的專家論證會。原來的規劃中,這條大馬路的容積率是2.5,意味著旁邊樓房的高度為25米左右,會把
民國時期的文物遺跡都‘蓋住’,但在專家論證會上,建設方主動提出來,把容積率降為1,也就是說旁邊建築的高度降低為10米至15米高,要讓民國建築露臉。”薛冰說,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情,這說明,大家都是有心保護文物,文物為重。
南京大學教授賀雲翱說,這是建設和文保之間的一種理性傳遞,在文明進程中,建設和文保會不斷取得共識。“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大家的見解會慢慢趨同,不是權大嘴巴就大,錢多嘴巴就大,而是在建設和文保間,找到共識,相互協調。”
首次吸納高校師生
參與歷史風貌區的規劃
“南京的文保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階段。”南京市文廣新局相關負責人說,現在,南京市的建設項目涉及到全國重點文保單位的,都會主動上報國家文物局,走程序。盡管地鐵5號線選線方案被國家文物局要求修改,但對南京來說,這是一次進步。
南京規劃局名城保護處相關負責人介紹說,“以前地鐵遇上城牆,想穿就穿了;但現在會想到上面有城牆,我得小心一點,謹慎一點,態度上有了轉變。”
在規劃上,南京也不再是專家說了算,而是首次吸納高校師生志願者參與歷史風貌區規劃保護與復興。今年,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的師生志願者們,對小西湖片區進行了調研,陰暗潮濕的老宅子下雨就漏水,沒有起碼的廚衛配套……這裡的建築雖然基本保留了明清時期的空間格局,但環境差,公共配套設施缺乏。這裡該如何改造? 志願者們在小西湖片區泡了111天,並且交出了答卷,為這裡的老房子設計了規劃方案。
多年高度關注老城南保護與復興的南京大學青年學者姚遠表示,這一創舉將成為國內城鄉規劃公眾參與的一個裡程碑。
未來
近現代建築有望
在“十三五”納入保護
從1984年第一版名城保護規劃到2012年第四版規劃,保護對象有了很大拓展。南京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童本勤介紹,不僅是文物點的保護,而且拓展到了街區、古鎮古村、重要的近現代建築、非文物的一些民居,都列入了保護對象,對老城也提出了格局整體保護的要求。
據介紹,南京城牆外圍的工業遺產和古鎮古村,在第一版和第二版規劃制定時,可能才剛建好,不算遺產。三十年過去了,現在也被列為保護對象,共同反映南京發展歷程。
相關負責人透露,近現代建築也是南京的一種特色,打算在“十三五”期間保護起來。另外,老城南的打造也會繼續,包括荷花塘歷史文化街區和小西湖歷史風貌區都會繼續推進。相關負責人透露,“現在還在做方案,但保留原住民和老南京生活的宗旨不會變。”
南京大學教授賀雲翱介紹說,現在南京各個區縣對於文保也越來越重視。江寧區邀請以賀雲翱領銜的專家團隊制作了一個200余處物質遺產的全覆蓋保護規劃,從今年開始,江寧區每年會拿出500萬來落實保護規劃的實施。“這個保護規劃,是從現在一直到2030年的,把不同的物質遺產設計了20多種方向,有的可以變成遺址公園,有的可以變成博物院,有的變成社區小品……這種做法,在全國都是領先的。
對話著名文保專家蔣贊初
多年呼吁
有遺憾,也有欣慰
冬日暖陽讓房屋變得明亮。88歲的蔣贊初面前堆放著很多報紙,他每天都在看報,關心外面的變化。說起南京的規劃論證會,他說出於年齡、身體的考慮,從去年開始已經不去參加南京的規劃會了。
改革開放後,蔣贊初被聘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專家組成員、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組成員和南京規劃委員會委員。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在為南京文保鼓與呼。“有痛心,也有欣慰。”這是蔣贊初對南京文保的感受。
現代快報: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文物保護工作的?
蔣贊初:大概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中山南路南延,首當其沖的,就是老門東、老門西。但我們知道消息時已經晚了。真正第一次參與保護,是在90年代張府園小區建設時。當時,施工方挖出了一條南唐皇宮護城河的遺址,石頭駁岸很完整,建議列入省級文保,保護下來,但最後以失敗告終了。這讓我感覺非常遺憾。
現代快報:文保這麼困難,為什麼還要這麼堅持?
蔣贊初:能保多少就保多少吧,總不能眼看著不說。
現代快報:這麼多年下來,您的感受如何?
蔣贊初:有遺憾、有痛心,也有欣慰。南京明城牆保護得非常不錯,近現代建築也保護得不錯。感到最欣慰的是,六朝博物館建成對公眾開放了。六朝是南京非常重要的時期,當時的皇宮就在現在的南京圖書館、六朝博物館一帶。2008年6月,因為發現六朝建康城的城壕,我建議在遺址范圍內建立一座“六朝建康都城遺址博物館”,以原地保護一段外包磚的夯土城牆以及附近遺址中發現的重要遺跡和遺物,如磚鋪道路、石柱礎、瓦當銘文磚與釉下彩瓷器等。這個建議經過6年的醞釀、磋商與籌備,終於在2014年8月,以“六朝博物館”之名得以實現,也算實現了我的部分夙願。
還有南唐伏龜樓。伏龜樓建於南唐或稍早的楊吳時期,是一處集軍事防衛與登高觀景於一體的遺跡,是目前南唐建都金陵時期城內唯一幸存的遺跡。現在伏龜樓保護了下來,而且對公眾進行展示,不容易。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