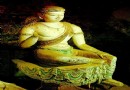感受人才輩出的許村
日期:2016/12/15 0:06:01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清晨的迷霧中,坐車從歙縣出發,沿著歙許公路一路向東北方向行駛,富資河蜿蜒相伴流淌,公路兩旁有成片的甘蔗田和菊花田。一路過了富竭、徽城,無數的村中靜默著。擦肩而過的行人也不多,只有汽車的馬達聲和車窗的震蕩聲在耳旁連綿不休。過豐口村的時候,太陽已經升起來了,薄霧散盡,富資金河也開始了一天的流光溢彩。
一路顛簸到了許村,村長正在橋頭值班,他是個熱情干練的人,十分熟谙本村的文史。買了票後,因為幾乎沒有游人,所以他便帶我進村去看。
許村地處古徽州府和安慶府之間的徽安古道上,北面便是黃山的主脈箬嶺,舊稱富資裡,亦名昉溪。南梁時,新安太守任昉羨慕此地山川絕佳,卸任後便隱居在此。之後,唐朝戶部尚書許儒為避戰亂,亦遷居於此,其後人繁衍成為當地巨族,是為許村。明清時期,許村已貴為徽州第一進士村,歙縣“許國坊”的主人許國即許村許氏後裔,在近代更是出現了一門五博士四院士的盛況。

高陽橋
進村必過昉溪之上的高陽橋。許村高陽橋為雙孔石墩廊橋,裡面掛著一塊“永鎮安流”的橫匾,橋柱下是一溜的大紅燈籠,其南側佛龛裡供奉著一尊姿態安詳的南海觀音菩薩。透過廊橋上的圓孔窗洞可以看見昉溪兩岸遠遠近近、高低錯落的粉牆黛瓦倒映在昉溪中。陽光透過廊橋牆上的窗投射到廊橋中,從橋頭到橋尾,一字排開的圓形光斑在橋面上閃耀。聽著橋下汀淙的流水聲,走在廊橋光影剔透的空間中,仿佛感覺到了時光在安靜地流淌。
穿過高陽橋,迎面便是一座四柱三間五樓式的“雙壽承恩”牌坊,這是明代隆慶年間,朝廷為許村時年101歲的徽商許世積和其103歲的夫人宋氏一起立的“瑞侶”坊。坊柱上的倒爬獅子瞠目裂嘴,形象古樸,爬滿了蒼苔,一看便知道這是典型的明代石雕風格。承恩坊上的石雕無一不是長壽的祥瑞符號,石色蒼黃,刀法古樸,雖不夠細膩精巧,卻也栩栩如生。那上面的青苔斑駁了流年,經歷了雨雪風霜,灰了又綠,綠了又灰,寫滿了滄桑。
雙壽承恩坊前便是村巷,左轉是一座過街亭,名為大觀亭。過了大觀亭之後便是三間五樓的五馬坊,許村長解釋說,“五馬”是明代對知府的雅稱。五馬坊的造型極有氣勢,與大觀亭前後相對,位於同一條軸線上。這是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為許村籍福建汀州府知府、抗倭名將許伯升所立。
穿過悠長又斑駁的街巷,許村長帶我來到了許村歷史博物館,他說這裡原來是觀察第,明時為觀察使許天相的府邸,之後改為許氏宗祠。許氏宗祠為典型的徽派院落,前後三進,每進院落都是“四水歸堂”式,即天井四角的雨水順著天井四角歸流天井中。在徽州民俗理念中,水為財,所以‘四水歸堂”講究的是財不外流。

中進的正堂為敬愛堂,上懸“齒德達尊”、“大宅世家”等匾,正堂四面的牆上懸掛著許村籍的多位歷史名臣及大儒的畫像、生平介紹等。逐個看去,有唐宰相許敬宗、清大學士許國、末代翰林許承堯等,可謂名臣輩出。後進祠堂上懸有一匾“奮冀南天”,匾無落款及抬頭,僅有四字,從匾的文字及正文來理解,當是為紀念時任福建汀州府知府的許伯升而書。
據《許氏族譜》記載,許伯升兄弟一共六人,其六弟為許周安,年二十四歲卒,英年早逝,而其妻胡氏尚有遺腹子在身,許伯升便選了幾位老婦人來伺候弟媳婦,直到侄子出生。終胡氏一生,享年七十二歲,凜凜冰霜,不曾出門庭一步。清嘉慶年間於此地築祠以紀念許周安及妻胡氏,朝廷欲牌坊來旌表胡氏的貞德,因胡氏有遺願在先,不許立,所以作罷。在封建社會,朝廷的旌表對於一個因封建禮教而付出了極大代價的女人來說,應該是莫大的榮耀,可這卻不是胡氏想要的,胡氏的故事雖未留下一座實實在在的牌坊,卻令無數世人唏噓不已。
眆溪畔至今遺存的還有任公釣台、雲溪堂、大邦伯祠、薇省坊、三朝典翰坊以及西洋風格的許村儀耘小學等。建於明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的大邦伯祠尤其有氣勢,值得一看。祠堂前後共三進五開間,用了99根木柱,顯得恢弘壯觀。
風雨廊下掛著許家一門五博士四院士的介紹,許村長便挨個給我講,他說得很帶感情,眼裡滿是自豪。許家澤非常重視對下一代的教育,他的5個兒子個個非常優秀,創下了許氏一門同代留學人數之冠,這不僅是許村的奇跡,更是徽州空前的榮耀。我想起了先前路過的許家澤故居,不顯山不露水,不注意的話還真不知道那座門庭裡走出了這麼多風雲人物。許家的五個兒子分別是長子許本震(德國耶納大學哲學博士)、次子許本純(美國伊利諾斯州立大學工程研究院采礦博士)、四子許本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博士)、五子徐本謙(德國漢堡大學醫學博士)、六子許本怡(先後留學美、英,獲哈佛、倫敦等大學商業管理碩士學位)。五人學成歸國後,都成為所在領域的領軍人物,堪稱國家棟梁。不僅如此,在歷史的大是大非面前,許家也有著非凡的判斷力和清晰的抉擇。
許村的歷史人文遺跡眾多,人文傳統根生葉茂,薪火相傳。在徽州歷史的長河中,這樣的奇跡無可復制,它只屬於唯一的許村。
- 上一頁:雄村“五世一品”家族
- 下一頁:探尋黃田的洋船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