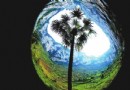從文物到文化遺產
日期:2016/12/14 19:03:19 編輯:古建築保護
兩千七百年來,文物概念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自有史記載以來,“文物”一詞最早出現在距今27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
當時各諸侯國日益強大,周王室逐漸勢微,禮儀制度正處於禮崩樂壞的危險邊緣。在這種背景下,“重德守禮”成為各國君臣之間經常討論的熱點話題。《左傳·桓公二年》記載魯國大臣臧哀伯規勸桓公的一段話中提到:“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其中的“文物”代表禮樂、典章制度的統稱,這一涵義一直沿用到秦漢以後。魏晉南北朝時期, “文物”一詞又增加了“文彩物色” “車服旌旗儀仗”等新的涵義。
直到唐宋以降,文物的涵義才開始接近今人的理解,有了古代遺物、古物的意思。如唐代顏師古《等慈寺碑》:“即傾許之人徒,收亡隋之文物。”宋代文天祥《跋誠齋〈錦江文稿〉》:“嗚呼!庚申一變, 瑞之文物煨燼十九。”北宋中葉,以呂大臨和李清照丈夫趙明誠等人為代表,以青銅器、石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金石學”興起,以後又逐漸擴大到研究其他各種古代器物,他們把這些器物統稱之為“古器物”或“古物”。及至清代,由於受到乾嘉學派的影響,金石學達到鼎盛。“古物”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大,銅鏡、兵符、磚瓦、封泥、甲骨和簡牍等都囊括其中,並擴及明器和各種雜器,稱呼也增加了“古董”“骨董”和“古玩”等。這些不同的名稱,涵義基本相同,它們與“文物”一詞常常替換使用。
民國時期,上述這些詞匯的概念和內涵比過去更為廣泛。如1930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古物保存法》明確規定:“本法所稱‘古物’是指與考古學、歷史學、古生物學及其他與文化有關之一切古物而言。” “文物”的概念已經不僅僅指向青銅器、書畫、碑帖等古代遺物,同樣也包括了古建築、古遺址、石窟寺等古跡遺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以及後來的國務院所頒布的一系列有關保護文物的法規,都沿用了“文物”一詞。但是指向卻不盡相同。直到1982年和200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兩次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才把“文物”一詞及其所包括的內容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文物的概念較之以往更為明確、具體。同時,為了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文物法還提出了“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館藏文物”和“民間文物”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分類方法,它們一直沿用至今。
關於“文化遺產”的663號提案
在1985年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一份由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教授倡議,陽含熙、羅哲文、鄭孝燮共同簽名,建議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663號提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是一份什麼樣的公約?為什麼我們要加入它呢?這還要從一年前說起。
1984年,侯老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他了解到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通過了一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這個公約針對全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受到破壞的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希望能通過提供集體性援助來保護這些屬於全人類的共同遺產。公約對“文化遺產”的定義有紀念物(monuments)、建築群(groups of buildings)、遺址(sites)三條。按照公約中的定義,中國的許多文物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條件,我們是不是應該放眼世界,大膽地走出去,把中國的文物保護與世界相接軌呢?侯老心動了,如果簽署這份公約,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締約國對於保護祖國的文物意義將是多麼重大!
於是在1985年的政協會議上出現了這份663號提案,很快它又被送交給全國人大審議,同樣引起了與會代表的高度重視,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准中國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兩年後,“故宮”“長城”“秦始皇陵”“敦煌莫高窟”“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5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第一批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文物。
從定義上看,國際社會在1972年界定的“文化遺產”與我國的“不可移動文物”的概念更為接近, 而“可移動文物”在西方往往被視作藝術品。也許是因為“文化遺產”和“文物”的概念並不相同,“文化遺產”一詞在中國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和使用。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新世紀,在此期間,國際社會對於“文化遺產”的認識和理解並沒有停滯不前,隨著1994年日本《奈良真實性文件》等一系列文件的先後出台,文化多樣性和遺產多樣性被充分認識,“文化遺產”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大,它已經超出了“不可移動文物”所包含的有形的“物”的概念,還包括精神、意識、風俗習慣等無形的“非物質”的涵義,如歷史名城、建築物、考古遺址、文化景觀、實物以及各種慣例、表現、表達方式、知識和技能都囊括其中。
2005年1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全新的“文化遺產”理念開始指導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而隨即展開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也恰好成為這些理念付諸實踐的一次全面考核。
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是對“文化遺產”理念的一次全面實踐
2007年4月,國務院下發了《關於開展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通知》,決定對我國境內(不包括港澳台地區)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動文物進行普查。普查的技術路線強調對新的“文化遺產”理念的應用,要重視鄉土建築和建築群,大遺址和遺址群,跨省區的線形遺址和遺跡;重視具有典型價值的近代工業建築、金融商貿建築、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建築、水利設施、林業設施、交通道路設施、軍事設施等行業性質文化遺產,以及各種風格、流派、形式的近現代代表性建築等。
按照新的文物普查理念,過去許多曾被忽視的文化遺產都被納入了登記的對象。
例如在江蘇興化城區東郊、裡下河腹部,有一片由古潟湖逐漸淤積而成的湖蕩沼澤地帶。先民們利用湖沼中一個個大小不等、形態各異、高低錯落的土丘,壘土耕種,逐漸形成了大面積的“垛田”。到1986年,興化境內共保存歷代垛田4.8萬畝。這些垛田互不相連,從遠處看似乎漂浮在水面上。春暖時節,油菜花開,無數塊垛田便形成了“河有萬彎多碧水,田無一垛不黃花”的瑰麗景色。江蘇興化的垛田不僅體現了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同時又與自然環境相融合,形成了人文、自然復合的“文化景觀”。它已被列入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文物的名錄。
從時間上看,過去對文物的認定往往根據時間的遠近,如果不夠“古老”就不屬於文物,就不需要保護。而這次普查並沒有嚴格地限定時間,只要在普查標准時點2007年9月30日之前,凡是具有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且實際存在的不可移動歷史文化遺存,均應被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
從空間上看,過去對文物的認定往往局限在單體的“點”或“面”上,這次普查將空間范圍擴大到更加廣泛的“大型文化遺產”、“線型文化遺產”和“文化線路”、“文化空間”上面。
從要素上看,過去的認定往往著眼於單一文化要素,而不重視自然要素。這次普查將兼具文化和自然復合特征的“文化景觀”也一並納入。
從類型上看,過去的認定往往著眼於“靜態遺產”,認為文物一定是不可再生的,靜止不變的。現在以新的理念看,它完全可以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和充滿生活氣息的,像古代的運河、種植業、酒窖、工廠、歷史文化街區、歷史文化村鎮等仍保持著原有使用功能的“活態遺產”也被納入到普查的范疇。
從價值上看,過去的認定往往重視皇家宮殿、帝王陵寢、廟堂建築、紀念性史跡等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築,重精英文化、正統文化,這次普查將反映普通民眾生活、生產方式的“民間文化遺產”,如傳統民居、鄉土建築、老字號、工業遺產等也記錄下來,真實地還原歷史。
劉慶柱認為:“歷史是多面而立體的。把時段拉長,把視角放寬,才能更客觀、更全面地檢視歷史……”,單霁翔提出:“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其言是也!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