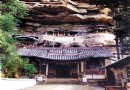番茅黎寨的黎家女子織錦
日期:2016/12/14 23:56:54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黎錦就是海南島的黎族織錦,剛到海口第一天,我就慕名去了海南省圖書館裡的黎錦坊,可惜那裡的黎錦雖美,卻因陳放的環境過於華美而顯得有些別扭,況且黎錦本身是黎族女子的衣飾,衣服的主人不見了,只是幾件漂亮的衣服掛在空蕩的大廳裡,始終感覺空洞而無趣。一直想象在一個椰林環抱的黎寨裡邂逅一群女子,無論活潑天真的小女孩,還是豆蔻年華的姑娘,或是飽經風霜的老阿媽,她們都穿著自己親手編織的筒裙、對襟花衣,頭披五彩花巾,纖細的腰間系著寬腰帶,織錦上或有星雲日月,或有稻草花木,或有著春光燦爛的田園景象,或有著持弓握箭保衛鄉土的勇士,那些美麗的女子在寨子裡款款腰身,穿行在田間屋捨,那該是一幅多麼攝人心魄的畫面啊!
帶著這樣的想像,我來到了五指山市旁邊的番茅黎寨。寨子離市區不過二三公裡,沿著市區中心的南聖河慢慢踱步,在一片椰林的掩映下,就看到了番茅黎寨。寨子其實已經很破舊了,20世紀末時番茅黎寨曾經被規劃成旅游區,試圖建成黎族民俗文化村,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又半途而廢,民俗村搬去了三亞,番茅黎寨被大開發的浪潮遠遠地拋開了。於是所謂的“船型草屋”沒有了,跳黎族舞蹈的表演團隊解散了,為旅行團專門搭建的竹樓也塌了。好在劉香蘭一手組建的黎錦教習所還在,現在我們到番茅黎寨,還能看到原汁原味不帶任何表演性質的織錦場面。

到番茅黎寨時已是午後了。黎錦教習所設在寨子村委會的文化室裡,一間普通的平房,地板上鋪著瓷磚,十幾名婦女正在席地而坐,低著頭自顧自地忙著手上的活計,有的在分線,有的在看圖樣,有的在編織,見我進來,只是抬頭羞澀地笑笑,她們黝黑的臉上滿是善意。劉香蘭就坐在這群女子中間,微胖的體型,臉上笑意盈盈,這一天,她沒有在織布,只寒暄了幾句就匆匆出去了,說下午縣裡有個會要開。2010年6月,劉香蘭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黎錦的國家及代表性傳承人,她的黎錦教習所也漸漸有了名氣。黎族女子關於黎錦的最初記憶,大都始於幼兒時代,每一戶黎家,無論是母親、祖母,還是外婆,。所有年長的女子一定都有一套織黎錦的工具,她們把這工具叫做腰織機。這種由一根棍子和一些大大小小的木片木棍組成的簡單工具,使用起來卻非常考驗女子的腰力和腳力,因為在織布的時候,腰上要綁著籐腰帶,雙足要用力踩著經線木棍,右手持木刀,左手投引線,一坐就是大半天,這樣的姿勢和強度下,很多女子的腰椎都勞損成疾。劉香蘭十三歲隨母親學織錦,15歲開始獨立織布,2005年劉香蘭和寨子裡的其他十幾名婦女一起,成立了番茅黎寨織錦公司,自己生產和銷售黎錦。現在,教習所裡的婦女每個月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同時還能兼顧農活和家務,看上去大家的心情都很不錯。不過最令劉香蘭感慨的還是自己而是隨處可見的黎錦,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裡,竟然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走向了消亡,以至於需要用大量的社會力量,到處呼吁,到處宣講。
也許這就是現代社會發展需要付出的代價吧,總有一些傳統的東西要被高速運轉的列車甩出,遠遠的拋棄,而我們,坐在這兩高速列車上的人,又能為此做些什麼呢?從番茅黎寨回到五指山市區,我專門打了一輛摩的去海南民族博物館,希望了解更多黎族的歷史和文化。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博物館的大門緊閉,而且門楣殘破,從門縫望進去,裡面灰塵滿布,空無一物,顯然已經倒閉多時,令人不勝唏噓。站在瓊州大學所在的山頂望去,這座城市的西面已被辟成新區,一個個房地產項目正拔地而起,這是一個忙於賺快錢的享樂時代,至於這個民族的歷史,就快要被人遺忘了。

旅游貼士:
番黎茅寨離五指山市區很近,乘坐摩的即可到達,或者從汽車站對面那條路右拐,沿南聖河步行大約二十分鐘就到了。
現在黎寨裡的婦女們平時都穿這普通服裝,除非到了三月三等盛大節日,或者有電視台來拍片子,否則已經很少能看見身穿全套民族服裝的身影了。
織錦教習所的婦女一般下午在這裡織錦,上午在家忙家務和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