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陵
日期:2016/12/15 15:31:18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漢司馬遷《史記》中載:“黃帝崩,葬橋山。”橋山黃帝陵始創於漢代,橋山因山形像橋而得名,山上古柏參天,山水環抱,面積333公頃,山上6萬株古柏參天遍野,長青不凋。黃帝陵在橋山之顛,陵前所刻“黃帝陵”三字,是1958年郭沫若所寫。傳說黃帝活了110歲,天宮中的玉皇大帝派了一條巨龍接軒轅黃帝升天,人們把黃帝和巨龍團團圍住,依依難捨,巨龍馱著黃帝昂首升空,慌亂間有人扯住黃帝一塊衣襟,有人拽下一只靴子,有人拉住了黃帝佩劍,後來,把這些黃帝的遺物埋葬在橋山之顛,這就是黃帝陵的由來。
漢司馬遷《史記》中載:“黃帝崩,葬橋山。”橋山黃帝陵始創於漢代,橋山因山形像橋而得名,山上古柏參天,山水環抱,面積333公頃,山上6萬株古柏參天遍野,長青不凋。黃帝陵在橋山之顛,陵前所刻“黃帝陵”三字,是1958年郭沫若所寫。傳說黃帝活了110歲,天宮中的玉皇大帝派了一條巨龍接軒轅黃帝升天,人們把黃帝和巨龍團團圍住,依依難捨,巨龍馱著黃帝昂首升空,慌亂間有人扯住黃帝一塊衣襟,有人拽下一只靴子,有人拉住了黃帝佩劍,後來,把這些黃帝的遺物埋葬在橋山之顛,這就是黃帝陵的由來。
黃帝:黃帝姓姬,名軒轅,是距今約4700年前我國遠古社會的傳奇領袖,因崇尚土德,所以後人尊稱為黃帝。相傳他有25個兒子,分別得12個姓,後來的唐、虞、夏、商、周、秦都是這12個姓的後代;苗、戎、狄、毛、匈奴等少數民族都承認是黃帝的後裔,所以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尊他為中華民族的始祖,自己是黃帝的子孫,因炎帝與黃帝是近親,故又稱“炎黃子孫”。
 軒轅廟:傳統的南北縱深布局,進深340米。內有第一進院:黃帝手植柏(一棵近5000年歷史的古柏)、掛甲柏、碑廊(存40多通歷代帝王祭黃帝的古碑);第二進院:過殿中有孫中山先生的祭詞和毛澤東、蔣介石祭黃帝陵時所題的墨跡石碑
軒轅廟:傳統的南北縱深布局,進深340米。內有第一進院:黃帝手植柏(一棵近5000年歷史的古柏)、掛甲柏、碑廊(存40多通歷代帝王祭黃帝的古碑);第二進院:過殿中有孫中山先生的祭詞和毛澤東、蔣介石祭黃帝陵時所題的墨跡石碑
橋山:現有古柏81600株,其中千年以上數齡的有3萬多株,是我國最大的古柏林
漢武帝祈仙台:傳說漢武帝非常羨慕黃帝駕龍升天,在這裡祭拜黃帝後,對人說:“如果我也能像黃帝那樣乘龍歸天,仍下老婆孩子算得了什幺。”為了向蒼天表達他的祈求,武帝在黃帝冢前修築了祈仙台。
黃帝與中國文明
先秦兩漢時期的《逸周書》、《國語》、《左傳》、《莊子》、《管子》、《商君書》、《韓非子)、《世本》、《竹書紀年》、《呂氏春秋》、《大戴禮記》、《淮南子》、《山海經》等重要文獻都記載有黃帝的事跡。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孫胺兵法·勢備》,有黃帝作劍以及戰涿鹿之語。以上情況反映了黃帝的事跡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並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西漢司馬遷撰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時,收羅遣散的歷史傳聞,閱讀皇室所藏圖書、檔案。對黃帝、堯、舜的遺跡進行了調查,聽到的民間傳說也不違背古文記載。於是以《大戴禮記》中的《五帝德》、《帝系姓》兩篇與《國語》、《左傳》相印證,認為黃帝、颛顼
、帝譽、堯、舜的事跡可信,對百家之言,長老口碑,則擇其言雅馴者,才寫了《五帝本紀》,冠於《史記》書首,作為中國可信歷史的開端。
 這既反映了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對古史的認識,對史料的態度和寫作方法,也是對中國古史研究的貢獻
據《國語·晉語》載:“昔少典氏娶於有蛟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構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蠻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在那神農氏世衰,部落間戰爭紛起之時,黃帝以他聰穎的智慧,非凡的才華,開拓的性格,率領其部落,面對現實,習武為戰,保衛自己,興起於姬水,後沿洛水南下,東渡黃河,順中條山和太行山向東北發展,到達山西南部、山東黃河之濱及河北一帶。與此同時,炎帝部落興起於美水,其發展路線較黃帝偏南,沿渭水、黃河向東,到達河南。山東一帶。在氏族部落的不斷繁衍過程中,炎帝部落與東南的黎族部落發生沖突,炎帝戰敗,向黃帝求援。黃帝和炎帝聯兵,與蠻尤率領的九黎部落發生了“涿鹿之戰”,蠻尤敗北。戰後,炎帝恃強,欲侵凌“諸侯”,黃帝規勸無效,便發生了‘阪泉之戰”,炎帝戰敗。在那亂世中,凡有不順者,黃帝就從而征之,以戰爭手段制止了部落間的長期混戰,統一了黃河流域的大片土地,“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伐神農氏,是為黃帝。”《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修德振兵…··官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這就顯示了王國政治體制的初建。《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種五藝,撫萬民,度四方。”顯示了黃帝之時已從采集漁獵、漂泊流徙的‘“野蠻”生活,跨進銅石並用的農業經濟時代。《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獲寶鼎,迎日推莢”。其《索引》、《正義》說,莢音策,神策即神蓍,黃帝得蓍以推算歷數,於是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故日推策迎日。又說黃帝命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歷。《世本》載,黃帝令“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倉颌作書”。《說文解字·敘》說:“黃帝之史倉颌,…·‘初造書契。”以上記載顯示黃帝時已有歷法和文字。《史記·五帝本紀》還記載黃帝“曾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峻們,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於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這裡約略可見黃帝時代的疆域。以上文獻記載說明了黃帝的偉業和中華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
這既反映了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對古史的認識,對史料的態度和寫作方法,也是對中國古史研究的貢獻
據《國語·晉語》載:“昔少典氏娶於有蛟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構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蠻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在那神農氏世衰,部落間戰爭紛起之時,黃帝以他聰穎的智慧,非凡的才華,開拓的性格,率領其部落,面對現實,習武為戰,保衛自己,興起於姬水,後沿洛水南下,東渡黃河,順中條山和太行山向東北發展,到達山西南部、山東黃河之濱及河北一帶。與此同時,炎帝部落興起於美水,其發展路線較黃帝偏南,沿渭水、黃河向東,到達河南。山東一帶。在氏族部落的不斷繁衍過程中,炎帝部落與東南的黎族部落發生沖突,炎帝戰敗,向黃帝求援。黃帝和炎帝聯兵,與蠻尤率領的九黎部落發生了“涿鹿之戰”,蠻尤敗北。戰後,炎帝恃強,欲侵凌“諸侯”,黃帝規勸無效,便發生了‘阪泉之戰”,炎帝戰敗。在那亂世中,凡有不順者,黃帝就從而征之,以戰爭手段制止了部落間的長期混戰,統一了黃河流域的大片土地,“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伐神農氏,是為黃帝。”《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修德振兵…··官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這就顯示了王國政治體制的初建。《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種五藝,撫萬民,度四方。”顯示了黃帝之時已從采集漁獵、漂泊流徙的‘“野蠻”生活,跨進銅石並用的農業經濟時代。《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獲寶鼎,迎日推莢”。其《索引》、《正義》說,莢音策,神策即神蓍,黃帝得蓍以推算歷數,於是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故日推策迎日。又說黃帝命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歷。《世本》載,黃帝令“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倉颌作書”。《說文解字·敘》說:“黃帝之史倉颌,…·‘初造書契。”以上記載顯示黃帝時已有歷法和文字。《史記·五帝本紀》還記載黃帝“曾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峻們,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於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這裡約略可見黃帝時代的疆域。以上文獻記載說明了黃帝的偉業和中華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
根據文獻記載探索黃帝與中國文明時,若證之以考古發現和研究,則不難看到兩者之間的關系。十年前,我們曾主張黃帝時代相當於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晚期,也用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相佐證,今仍堅持原來的觀點,不再贅述。我們相信,隨著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的“遍地開花”和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黃帝是中華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將會被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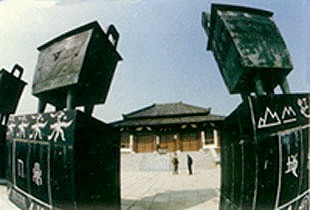
黃帝與神話傳說
黃帝時代,文字尚未成為歷史的載體,今所見有關黃帝的文獻是經過世代口耳相傳,到先秦兩漢才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內容比較復雜,其中既有先民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有演化了的情節,還包含著一些神奇的色彩,因而被稱為神話傳說。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先民對自身周圍的一些自然、社會現象無法理解,認為是某種神秘的力量所致,於是就根據自己的經驗構思它的形象及活動,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和社會,這就導致了神的崇拜,並以神意看待自然和社會的變化。因百,現實生活中具有傑出才能和高尚品德並被大家擁戴的英雄人物,經過人們神異性的升華變成為多智多能的神,從而後人在他身上所見更多的便是凡人所不具備的神奇性,這也是東西方古老民族發展歷史上的共性。
正由於黃帝是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一位傑出的代表人物,在傳說中既闡述有他的真實事跡,又將他說成是無所不能的天神。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內容被人們一代一代地傳頌著。如果說在古代由於人們認識水平的限制和感情上的需要以及“神權”的影響,而將黃帝神化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現代的中華兒女就沒有理由和必要再按照被神話化或演化了的模式來理解、稱道和傳頌黃帝。
但是,我們還應該了解,遠古的神話傳說是人類童年的一種創造,既反映了先民天真進取的生活與執著的追求,也反映了那一時代的稚氣和局限,其產生與當時社會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說,遠古的神話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性質,或者說具有歷史的成分。正如拉法格論述神話傳說的史學價值時說:“神話既不是騙子的謊話,也不是無謂的幻想產物,它們不如說是人類思維的樸素和自然形式之一。只有當我們猜中了這些神話對原始人和他們在許多世紀以來喪失掉的那種意義的時候,我們才能理解人類的童年。”(《宗教和資本》)。
黃帝作為遠古時代的人物,我們要研究他勢必要依靠神話傳說。在處理這種問題時,要以現代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認識為基礎,從當時人類社會的生活狀況來剖析神話傳說。也就是說要用歷史說明神話傳說,而不是用神話傳說來說明歷史。例如《大戴禮記》載:“宰我問於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以人也?抑非人也?何 以至三百年乎?’對日:‘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 年。”’又據《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屍子》雲:“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 孔子日:‘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謂之四 面也。”’上述孔子的回答是合理的。不能說黃帝是神,活了三百年,有四張面孔。例二 例於·黃帝》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罴、狼、豹、貙、虎為前驅,雕、 鹖、鷹、鸢為旗幟。”這條資料應解釋為:黃帝率領著以熊、罴、狼、豹、貙、虎為圖 騰的部落,揮舞著用雕、鹖、鷹、鸢的羽毛制成的旗幟,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因為在 遠古時代,部落都各自有圖騰,而這些圖騰多取自動物或無生物的名稱,如蛇圖騰、龍 圖騰、鳳圖騰、雲圖騰等。用鳥的羽毛作旗幟,在後世也仍有使用,如李斯在《谏逐客 書》中的“建翠鳳之旗”,意即樹立起用翠羽編成鳥形狀的旗幟。這樣的解釋,想來符 合於當時的實際情況,今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不能說成是黃帝卒領著熊、罴、狼等動 物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例如《管子·輕重》載:“黃帝作鑽隧生火”,《周易·系辭》載: “黃帝作弩”。據考古發現所知,早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已發明了用火,火的使用“第一 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把人和動物分開”(恩格斯《反杜林論》)。根據古人類 用火遺跡判斷,距今170萬年的“北京人”雖不會人工取火,還處在保存天然火種階段,但距今50O00年的“河套人”已發明了磨擦生火的技術,使火能更有效地為人們服務。關於弓箭的發明,也早在黃帝之前,“山頂洞人”遺址和大荔沙苑遺址發現的矢镞都是明證。因而,我們就不能附和這類文獻記載,將原始社會早期和晚期的發明創造混為一談,記在黃帝的名下。
總之,在黃帝的研究上,對於古文獻的記載,信,就要信而有征,信而合理,不能輕信和迷信,不能將黃帝說成是神,也不能將黃帝生活的歲月說成是中國古史的黃金時代;疑,就要疑而有據,疑而合理,不能武斷和迷疑,不能因為神話傳說中有矛盾或者具有神奇色彩,就否定黃帝的人格以及他是中華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