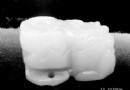重新認識古代國家形成標志
日期:2016/12/14 18:29:42 編輯:仿古建築材料
研究國家起源和發展,必然涉及國家的定義與國家形成的標志。關於國家的定義,國內外學術界沒有統一說法。筆者的《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一書,提出可將“古代國家定義為:擁有一定領土范圍和獨立主權、存在階級、階層和等級之類的社會分層,具有合法的、帶有壟斷特征的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強制性權力的政權組織與社會體系”。
研究國家起源和發展,必然涉及國家的定義與國家形成的標志。關於國家的定義,國內外學術界沒有統一說法。筆者的《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一書,提出可將“古代國家定義為:擁有一定領土范圍和獨立主權、存在階級、階層和等級之類的社會分層,具有合法的、帶有壟斷特征的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強制性權力的政權組織與社會體系”。這裡,將“政權組織”與“社會體系”並列,是因為筆者贊成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的“國家”具有雙重含義,它有時指政府機構或權力機器,有時卻又指歸這種政府或權力所支配的整個社會體系。國家的定義與國家形成的標志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
傳統標志說有待辨析
最早明確提出國家形成標志的是恩格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提出國家形成的兩個標志,即按地區劃分它的國民和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沿用恩格斯的兩個標志說。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按地區劃分它的國民這一標准,並不符合古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如果按照恩格斯及其他西方學者主張的地緣關系作為衡量標准,中國商周時期依然沒有進入國家社會。為此,筆者提出:“國家形成的標志應修正為:一是階級的存在;二是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
對於筆者提出的國家形成的這兩個標志,近年來也有學者認為,階級的出現只是“國家產生的前提條件之一”,把“前提條件之一作為主體事物本身的標志,十分不宜”,並說有些社會“有了階級,國家並未產生”,如“中國的涼山彝族”(易建平《文明與國家起源新解—與范毓周、王震中等學者商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8月11日)。這一討論,顯然使問題的研究有所深入,但所帶來的問題也不能不辨。
首先,盡管可以存在只有階級分化而沒有國家政權的社會實體,但絕不存在只有國家政權而沒有階級的社會;不論是階級產生後才有國家,還是國家是隨階級的產生而一同出現,階級是國家的社會基礎,是國家社會的重要現象,這一現象既可以是“前提條件之一”,也可以是“主體事物本身”的標志之一。
其次,筆者並非僅以階級產生作為國家形成的唯一標志,而是把它與“凌駕於全社會之上強制性的權力的設立”共同作為國家形成的標志,二者缺一不可。以階級的存在作為國家形成的標志之一,有助於說明社會的嚴重不平等、社會的復雜化程度和國家權力的強制性。
再次,這一問題的提出者贊成馬克斯·韋伯有關國家的定義,但他認為韋伯定義中的國家“壟斷了”的“武力”直到近代也沒有完全實現,若以此為標准,近代中國尚不屬於國家社會,並認為韋伯這一定義只適用於“標准國家”(近代國家),而不適用於“早期國家”和“成熟國家”。筆者認為,從國家發展歷程上看,可以劃分“古代國家”與“近代國家”(民族國家);也可以有“早期國家”與“成熟國家”(發展了的國家)的劃分;還可以有“國家”與“前國家”、“國家”與“非國家”的區分,但都無法使用“標准國家”與“非標准國家”這樣似是而非的概念。因此,“標准國家”不具有科學性。此外,既然“韋伯的"國家"定義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那麼為何還要將其作為衡量其他定義或概念的標尺?
都城是國家的物化形式
以階級的存在和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強制性權力的設立作為國家形成的標志,屬於理論概念上的研究推進。理論需要聯系實際。先秦時期,一方面,建城乃立國的標志,最早的“國”指的是都城,也即《周禮》的“體國經野”,為此,筆者把中國早期國家稱為“都邑邦國”。另一方面,每個“都邑邦國”都有領土,在其領土內分布次級中心和不同等級的聚落。以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在地的都邑邦國為例,以陶寺都城為中心,有54處陶寺文化聚落遺址,並構成四級或五級聚落等級,其中包括次級聚落中心乃至再次級聚落中心。都邑邦國有自己的領土范圍,因各邦國實力差異而使其領土范圍和聚落群多寡不同,有的懸殊很大。總之,城鄉都鄙的國土結構不論是兩級還是多級組成,國都都是國家中心,也是國家標志、國家的物化形式。在這個意義上,考古發掘出土的早期國家都城對於國家與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我們主張以都城為國家形成的考古學標志,並非以有無城邑判斷其是否是國家。我們發現,在中心聚落形態階段就因戰爭加劇、防御需要而出現由城牆圈起來的城邑。例如,在南方,湖南澧縣城頭山在距今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屬於中心聚落形態發展階段,修築了環壕土城。在北方,距今53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鄭州西山城址和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城址,也都是中心聚落階段的城邑。如何判斷我國史前70余座城址,究竟哪些是中心聚落形態階段的中心聚落,哪些是早期國家都城?筆者以為需要附加一些條件並加以衡量。即一是當時階級產生和社會分層的情形,這可以通過發掘出土的墓葬等材料得以反映;二是城邑的規模和城內是否出現宮殿宗廟等特殊建築物。
一個龐大的城垣,需要組織調動大量勞動力,經過較長時間的勞動才能營建而成;城垣內宮殿宗廟之類的大型建築,也需要眾多人力物力資源,這顯示出在其背後有完善的社會協調和支配機制為其保障和運營。這就是通過修建城垣和城內宮殿宗廟建築所顯示出來的公共權力。然而,考古發現還表明,當一個社會出現社會分層時,雖修建了都邑城牆,但並非所有族人都居住在城內,城邑周邊還有一些村落亦即小的聚落,而城內宮殿也只是供統治階層和貴族居住。統治階層有權調動和支配整個聚落群的勞動力,顯然這種支配力具有某種程度的強制色彩。為此,筆者認為,只有當一個社會存在階層和階級時,城邑以及城內宮殿的出現,才可視為國家構成的充分條件。這種帶有強制性和壟斷特征的權力與當時的社會分層或等級相結合而構成的社會形態,完全不同於史前“中心聚落形態”,也不同於“酋邦”,而屬於早期國家。
標志之爭推進國家起源研究
對於上古史而言,學者對於國家形成標志的認識決定著其對國家形成時間的判斷和最早國家形態的認識。以筆者提出的國家形成的標志為標尺,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龍山時代就屬於中國的國家形成時期,其國家形態為單一制的邦國(或“古國”);堯舜禹“部落聯盟”也應改稱為“邦國聯盟”或“族邦聯盟”。堯舜禹都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本邦邦君(國君),亦為族邦聯盟的盟主。一些學者雖然不贊成以地緣關系取代血緣關系作為國家形成的標志,但沒有提出明確的國家形成標志,而是主張夏王朝為最早國家,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一系列的考古發現給我們提出新問題,也促使學者改變以往看法,如張光直先生在《中國古代王的興起與城邦的形成》,改變自己主張的中國的國家始於夏代,而認為從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龍山時代初期開始,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東海岸地區的平原河谷中分布著成千上萬的大小古國,這些古國內部已存在階級分化;國邑之內上層統治階級對下層階級進行經濟剝削。筆者相信,對國家形成標志的討論,必將帶動國家起源研究走向深入。
- 上一頁:明崇祯 青花千裡走單騎紋觚
- 下一頁:文物反映宋代居民生活